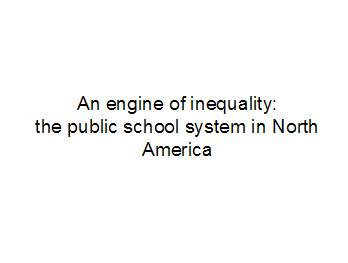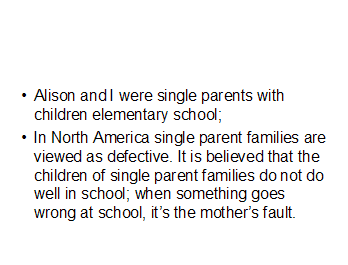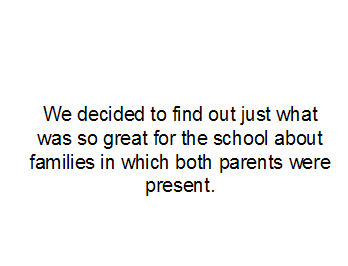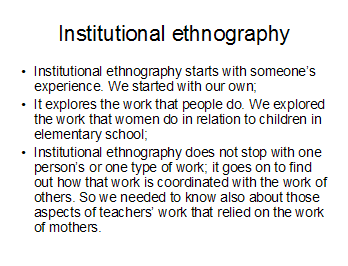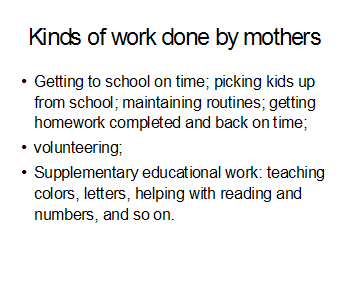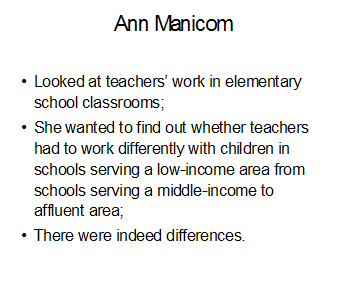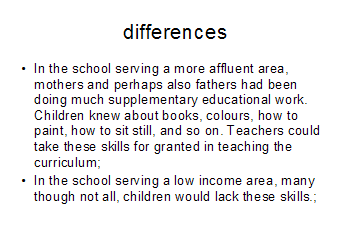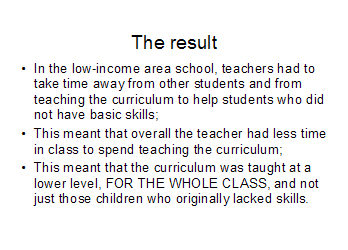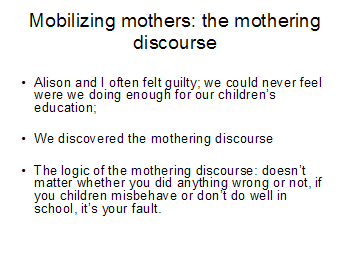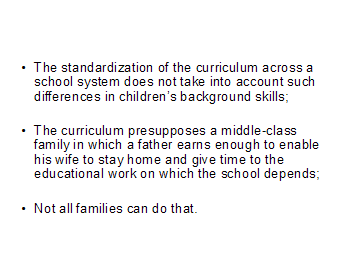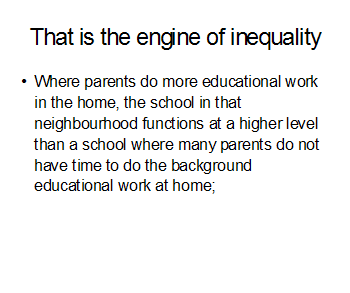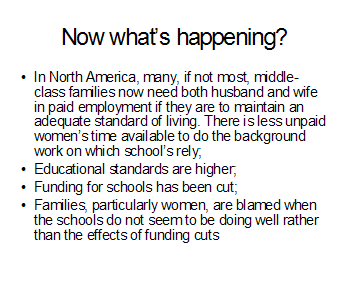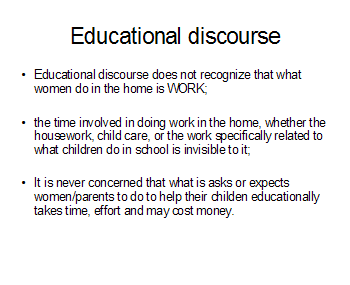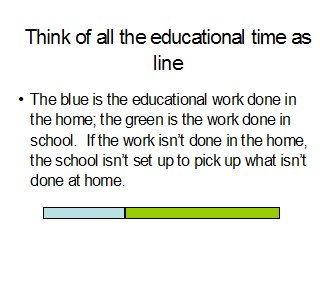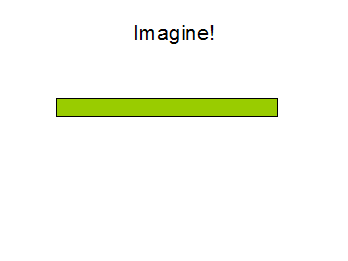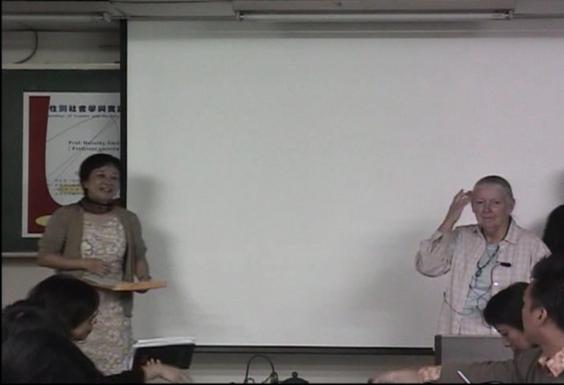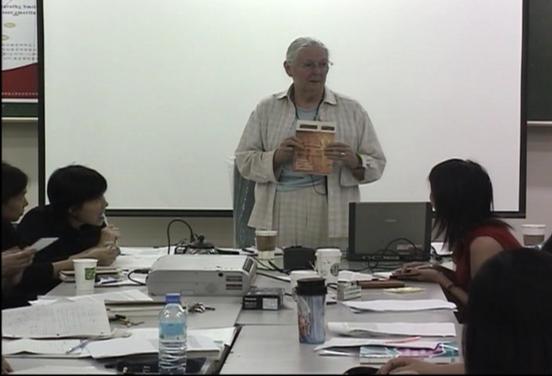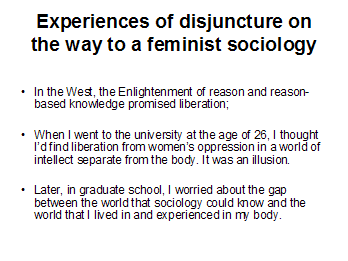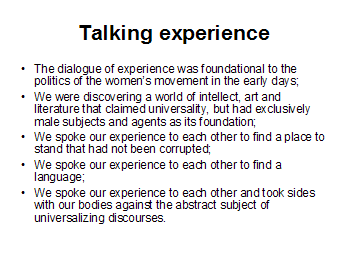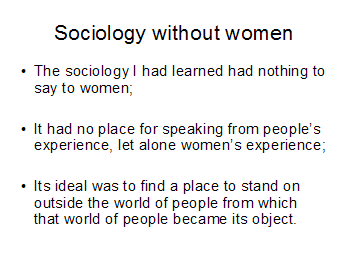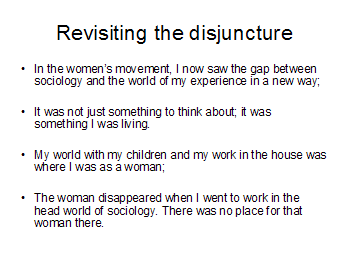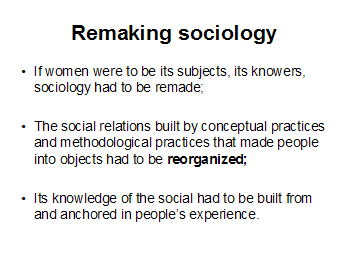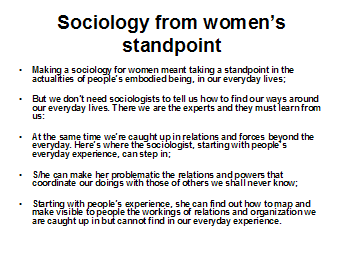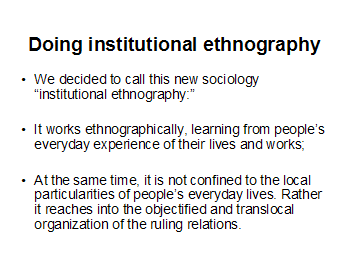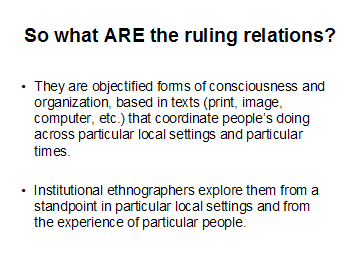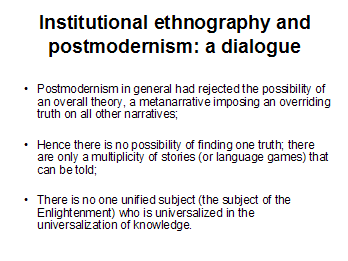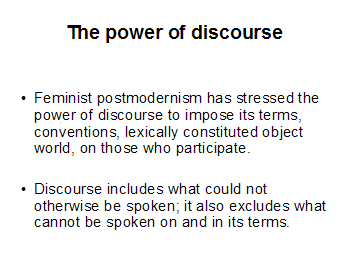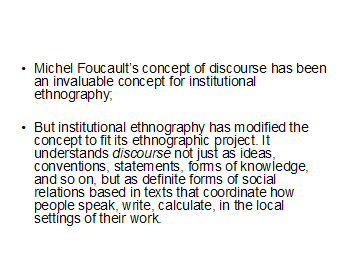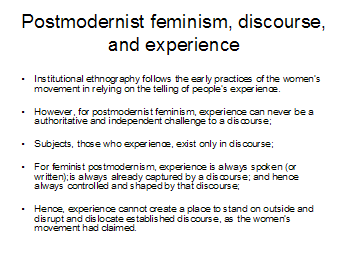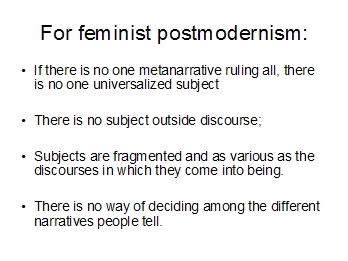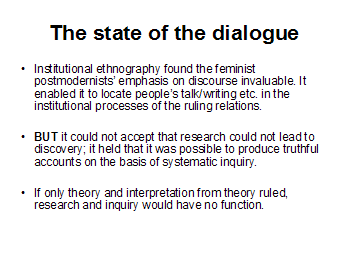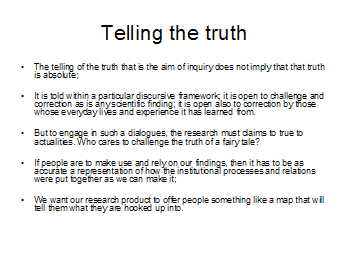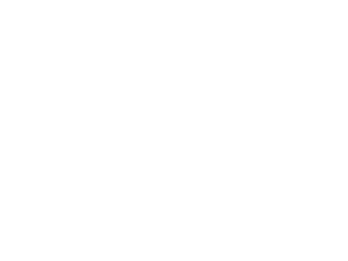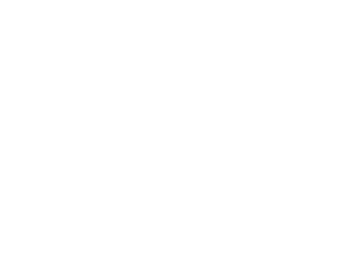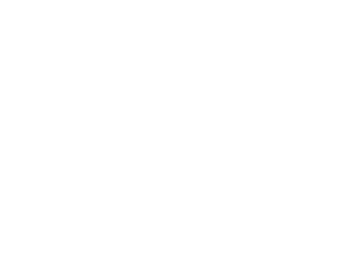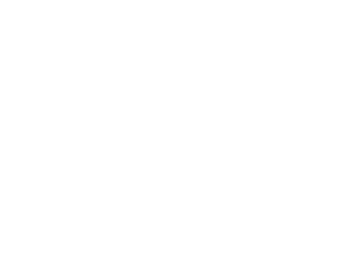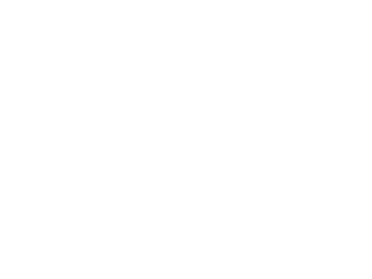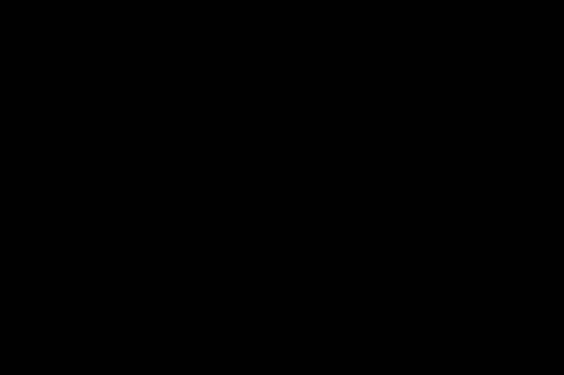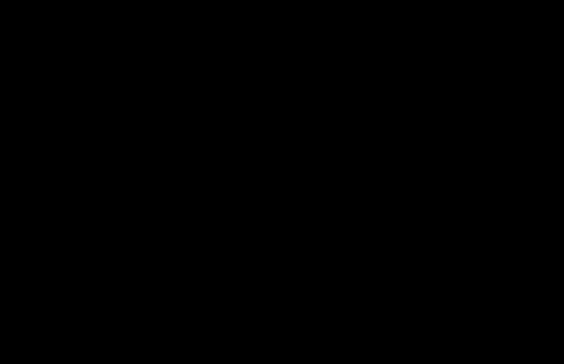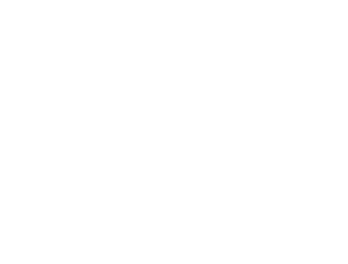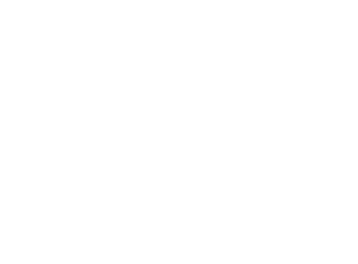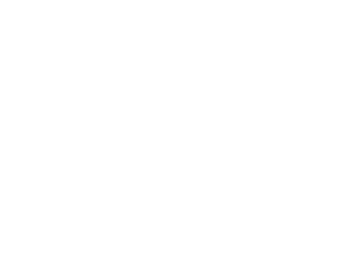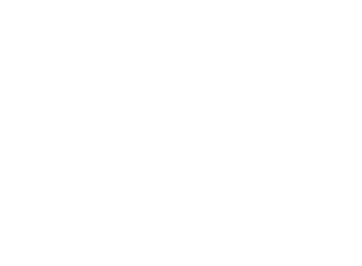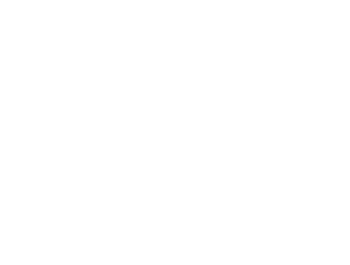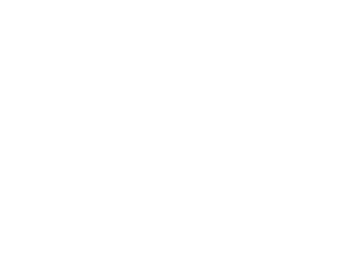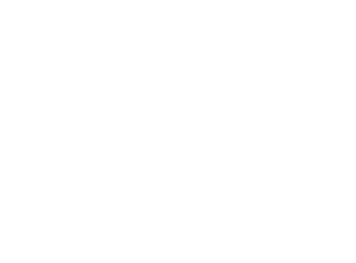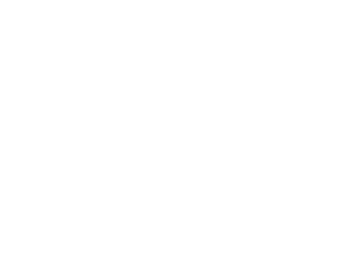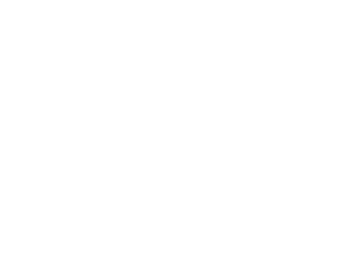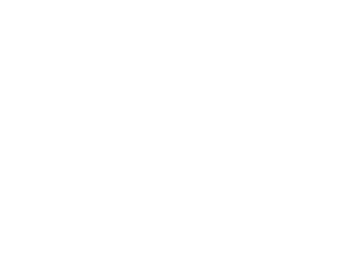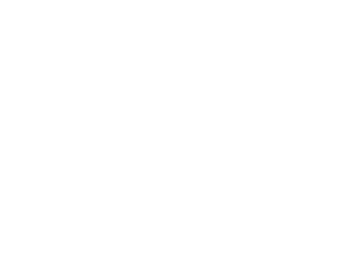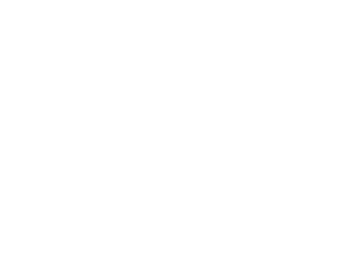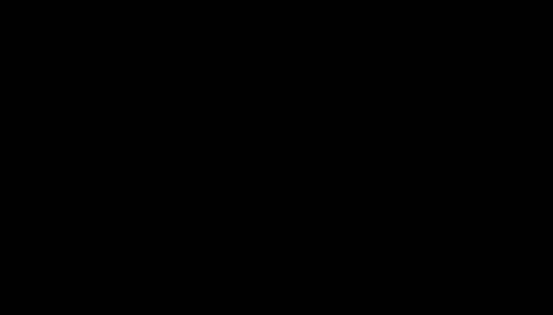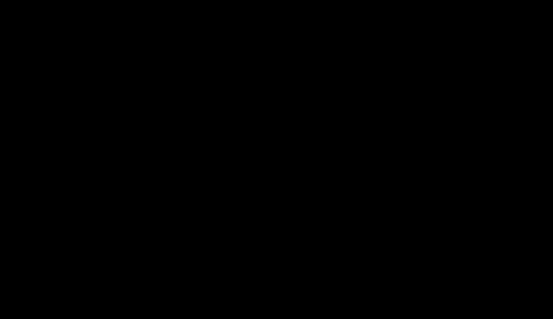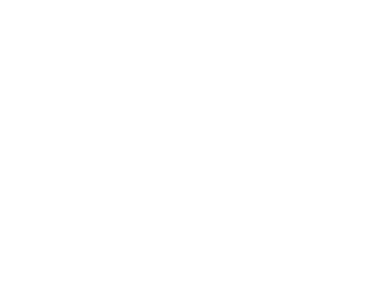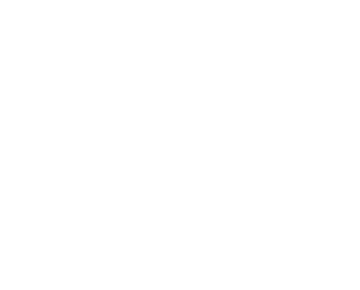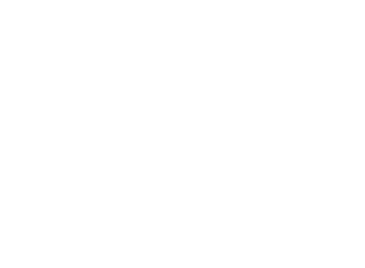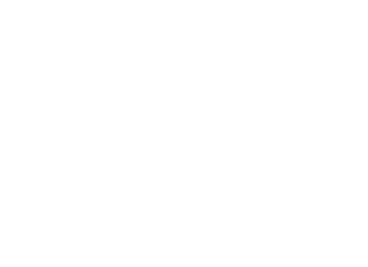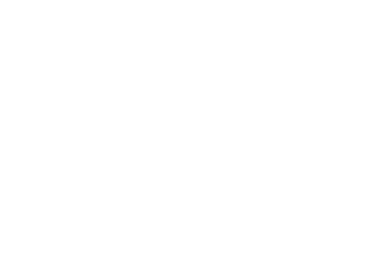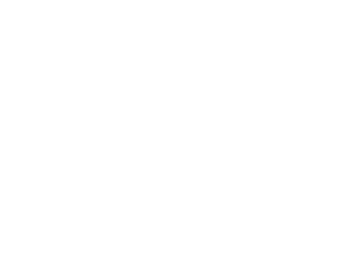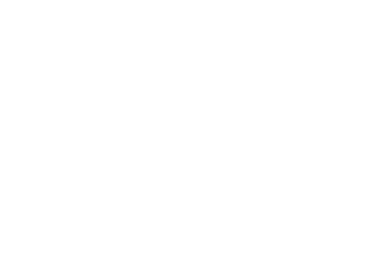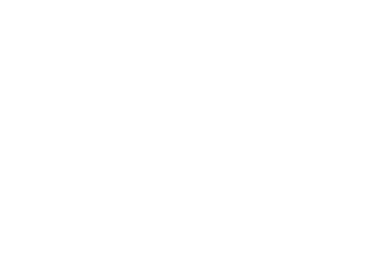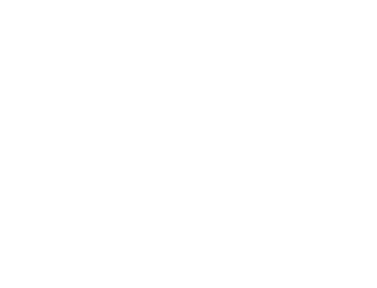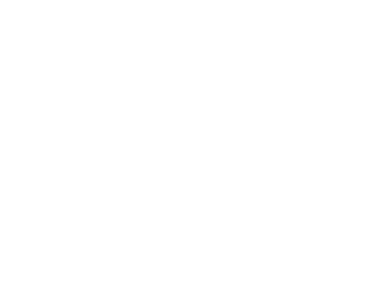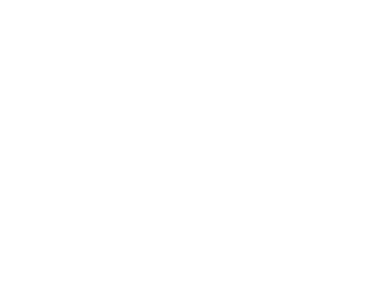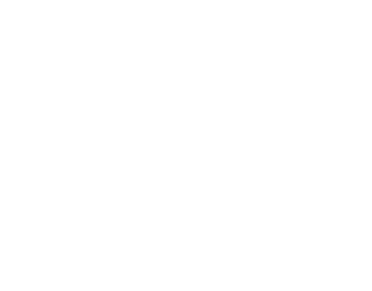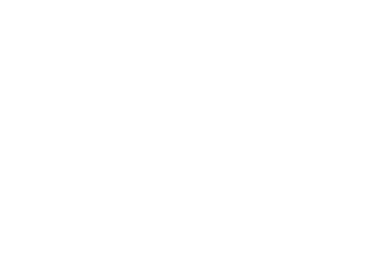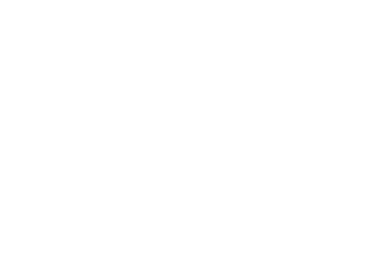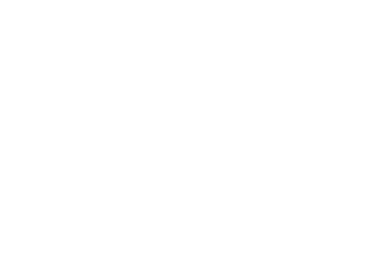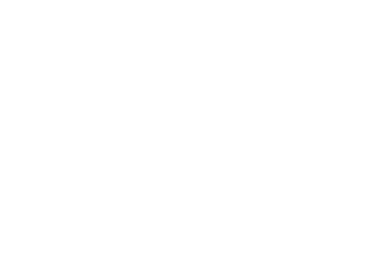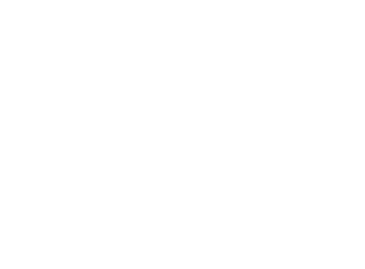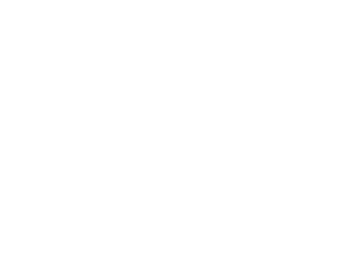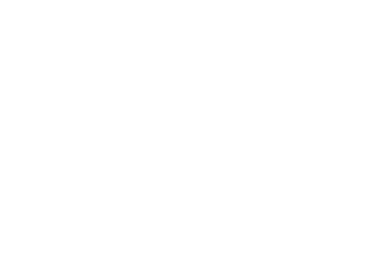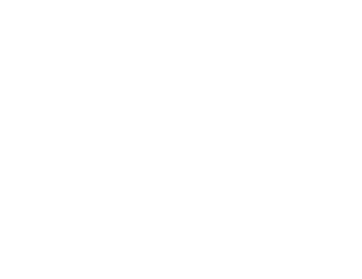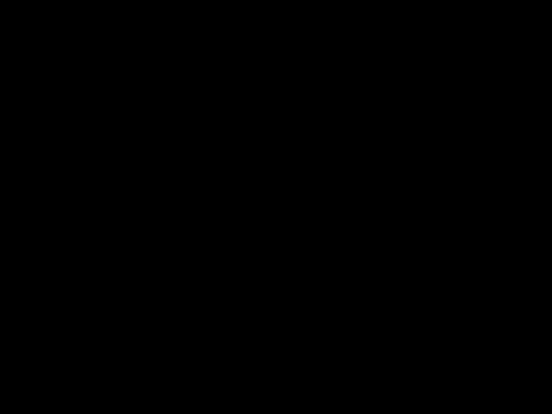v\:* { behavior: url(#default#VML) }
o\:* { behavior: url(#default#VML) }
.shape { behavior: url(#default#VML) }
教育部顧問室
「人文社會科學教育改進計畫」補助深度系列講座
(九一學年度下學期「性別與社會」個別型通識課程教學績優獎)
Dorothy E. Smith女性主義社會學講座(2004)結案報告書
1/5/2005
計畫主持人:唐文慧(成大政經所)
壹、講座簡介
本次深度系列講座邀請的學者Dorothy E.
Smith是一位享有國際盛名的女性主義社會學家。出生於1930年代,現年已經七十八歲。Smith教授約四年前已從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社會系退休,之前她也是多倫多大學性別教育中心的主任,長期從事婦女運動,並非常關心社會改革工作,結合學術研究與社會運動於一身,是典型七0年代的婦運學者的形象。
Smith
關心女性主義知識的建構與權力運作,曾特別以其創見提出了『組織民族誌』(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的觀念,獲得學術界和運動界的尊敬。這是一個可以應用在很多領域的知識建構的理論,她稱此為『女性主義研究的策略』,也在其專書之中有相當詳細的闡述,但是台灣探討此一研究方法和運用此研究取向所作的的經驗研究似乎仍舊不多。這次特地邀請她來到台灣,跟本地的女性主義學者和研究生直接對話,期待有機會能更為深入地瞭解她的理論精髓,和其在研究與教學實踐上的應用。
Smith批判傳統的社會科學研究通常是從文本媒介的論述(textually
mediated discourse)中,尋找一個觀點作為研究的起點,所以經驗與經驗主體都落在文本之外或之後,以致於使得社會學的論述長期以來,都顯得過於抽象,對於女人的行動與經驗通常都視而不見。這正說明了社會學論述的組成與她所謂的「統治關係」(the
relation of ruling)是共謀的。現有男流 (male-stream)的學術研究常常展現的抽象論述,正好也驗證了Smith所說的:在階級社會之中,「心智生產」變成了一種特權,是那些擁有與能夠支配生產工具,同時又佔用心智生產工具的階級所擁有的(Smith,
1987: 55),以致社會學論述變成只反映出組織者的經驗,而組織者又多為男性,於是男性處置、管理、組織或控制場面的經驗,成為一組強迫人們接受的知識範疇,羅織並強加於日常生活世界之上,成為思考與想像這一個世界的工具(Smith,
1987:55)。簡單介紹其思想與著作內容,以下並附上相關建議閱讀的參考書目給大家參考。
本計畫安排了全國各地共五場演講,包含南部兩場、東部一場、和北部兩場,與一場師生討論會,以下為演講和討論會記錄。
閱讀參考書目:
Dorothy Smith, The Everyday World as Problematic: A
Feminist Sociology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87)
Dorothy Smith, The Conceptual Practices of Power: A
Feminist Sociology of Knowledge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0)
Dorothy Smith, Texts, Facts, and Femininity: Exploring
the Relations of Ruling (London:
Routledge, 1990)
Dorothy Smith, Writing the Social: Critique, Theory, and
Investigations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9)
Griffith, A. I. & D. Smith (1991) Constructing
cultural knowledge: Mothering as discourse, in Women & education.
Edited by Arleue McLareu & Jane Gaskell (Eds.), Calgary: Detselig.
Griffith, Alison I. and Dorothy E. Smith
(2005,forthcoming) Mothering for Schooling. UK: RoutledgeFalmer.
Kathryn P. Meadow Orlans and Ruth A. Wallace Ed.,(1994)Gender
and the Academic Experience: Berkeley Women Sociologists,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貳、各校講座場次介紹
|
演講場次 |
演講日期/時間 |
主題 |
地點 |
|
一 |
11/17 WED
週三上午
10:00∼12:00 |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and Mothering for Schooling(「組織民族誌」:
以母職研究為例)
|
National Cheng-Kung University
成大總圖書館地下一樓國際會議廳 |
|
二 |
11/19 FRI
週五上午
9:30∼12:00 |
Sociology of Gender and
Its Practice(性別社會學及其實踐) |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高師大0307會議室
|
|
三 |
11/22 MON
週一上午
10:00∼12:00 |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and Feminist Experience in Academy(「組織民族誌」與女性主義學術經驗)
|
National Tai-Dong University
台東大學視聽教室D |
|
四 |
11/23 TUE
週二下午
13:30∼15:30 |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and its practice in Social Work (「組織民族誌」與其在社會工作的應用)
|
National Yang-ming University
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 |
|
五 |
11/24 WED
週三下午
15:00∼17:00 |
The Prospects of Feminist
Sociology 「女性主義社會學的前景」
|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台大社會系系館401會議室(女學會與性別平等教育協會合辦) |
註:以上五場演講之後,Dorothy
Smith還參加了11月25∼27日「亞太地區性別平等教育研討會暨工作坊」。並於11月25日(四)13:00-13:50的時間發表論文,主題為「Gender,
Schooling and the Training of Teachers in Canada」,地點在台灣大學新物理館國際會議廳(台大新體育館對面)。 詳細議程請見:http://ccms.ntu.edu.tw/~psc/
參、各校演講內容簡介
(一)、場次一:成功大學(11/17/2004)上午10:10∼12:00

照片說明:中間為 Dr.
Dorothy Smith,
右邊為主持人成功大學唐文慧教授,左邊為現場口譯者台南大學陳慧琴老師。

照片說明:於成大演講廳聽講之學生
演講內容:
今天的主題是Mothering for
Schooling,內容是談母職與學校間的關係,期待在今天演講結束後,大家可以一起討論,這樣一個在北美洲發生的情況,在台灣是否也有它的相關性。在演講開始前,要跟各位分享自己和朋友的自身經驗,我和我的研究夥伴都是單親家庭,通常這樣一個家庭的學生,會被定位成問題學生,很多老師會把學生的問題歸咎於他們來自單親家庭。所以我的同事和我想要瞭解,為什麼來自單親家庭的學生,會受到這樣的歧視,更重要的是在一個雙親家庭,它有什麼樣的特別?接下來介紹一下研究方法,這樣的一個方法,我們稱為組織民族誌,也就是不由理論或是文本開始,而是由個人實際經驗開始的一個研究。這樣的一個研究方法,是以個人的經驗為出發點,所以我們在這樣的研究中,研究母親實際的一個生活經驗,我們的研究內容不只是母親的經驗,還包括她的經驗如何影響到學校中教師的工作內容。根據我們跟母親間的面談,我們整理出母親平常做的例行性工作,而家裡有小孩的人可以瞭解到,一個母親在早上必須把小孩帶到學校,小孩回家時關心小孩的功課。根據我們的面談,我們發現並不是所有的母親都能以相同的能力,做到相同的程度的照顧,例如:有些母親晚上必須工作到很晚,所以她們的小孩早上常常會遲到。而研究中,我們比較兩個學校,一個學校是位在高所得社區,另一個學校則是位在低所得社區。我們發現在高所得社區的學校,有六十位的義工媽媽,相對於低所得社區的學校,只有一兩位的義工媽媽。這六十位的義工媽媽,做的工作內容包括:學校的一些行政工作、支援戶外教學或圖書館的活動等等。
我們的研究也發現,更重要的是母親也擔任一些基本的教育訓練工作,這些工作大部分是所謂的『幕後工作』,也就是家庭作業以外的工作,這些工作包括:在小孩子上小學前,學習怎麼分辨不同的顏色、學習注音符號、及基本的閱讀技巧、或是唸書給小孩聽等。而在這裡我也要跟大家分享,我另一位同事研究相關於這些基本的教育訓練工作的內容:
首先,他是以學校的觀點來研究,尤其是針對學校教師的工作,或是教師在教室裡面所必須要負責的工作。她想要瞭解,高所得社區的學校教師的工作內容,跟低所得社區的教師的工作內容,是不是有什麼樣的差異?而研究的結論是,不同社區的教師的工作內容有著相當大的差異。
因為來自高所得家庭的小孩,在就學前會有一些基本的訓練,例如:在閱讀時知道如何翻頁、如何坐好、如何拿筆等等。因為這些中產階級的小孩的父母親較多的時間來訓練她們小孩這些基本的技巧,而對老師來說,如果這些小孩的基本技巧都已經訓練好了,老師就可以不必花太多的時間在教導這些技巧,而花更多的時間在教學上面。這就是不同社區不同階級的學校,老師所必須承擔工作的差異。
因為來自低所得社區的的老師要花時間教導學生基本的技巧,再加上北美洲跟台灣一樣,每個老師都有基本的教學進度,這樣的結果顯示來自低所得社區的老師的教學成績沒辦法和來自高所得社區的老師的教學一樣的深入,也就是說老師必須要花時間教導學生基本的學習技巧時,會影響整個教學進度。
在我們的研究過程中,我們必須處理一個母職論述的理念,因為在此研究中和母親的面談過程中,常常會感到罪惡感,例如:我的同事在跟一位母親面談時,這位母親說她週末要帶小孩去參加一個莎士比亞的戲劇節,而透過這樣一個參與,她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教育孩子認識莎士比亞的戲劇。所以當面談結束時,我的同事感到很沮喪,因為她沒有辦法兼顧她自己的研究工作跟母親的職責,沒辦法跟小孩討論莎士比亞的戲劇,更沒時間帶小孩去參加這樣的一個戲劇節,所以我跟我的同事,決定去尋找這樣的罪惡感源自哪裡?我們找到這樣的一個母職的論述,這個論述在二十世紀初發展的,內容是不管妳有沒有做錯事,如果妳的小孩做錯事或是行為不好,這都是母親的責任。所以在一般的標準教育的課程規劃中,並沒有考慮到這種不同家庭背景對小孩學習技巧的差異。目前的標準是以中產階級為標準-一個全職的母親,或是父親都能參與這個基本的教育訓練,而發展出來的一個標準。而這樣是不公平的,尤其是當我們考慮到母職論述的實踐只能在中產階級的家庭,也就是當有一個全職母親能夠做這些事,才能夠實踐的標準。所以目前課程所設計的標準,沒有考慮不同家庭背景的小孩的學習情況,而這也是我所謂的不公平的機制。
在過去已經有很多研究在探討,母親的教育、母親的工作跟小孩個人學習過程之間的互動,但是我們這裡研究的重點是在,母親的工作如何影響學校。我們發現透過校長與老師的互動中,不斷地被認同,也就是我所謂的不公平的機制。
剛剛有提到母職論述是在二十世紀開始,在此同時許多公立學校被設立且很多教育政策,都是以中產家庭為主,其預設的立場是母親可以在家庭作這些基本學習技巧的訓練。而目前北美的現況是,第一:雙親都工作的情況越來越多,而在學校幫忙的情況也減少;第二:教育的標準同時提高,但來自政府的教育補助卻減少,在這樣的情況下,婦女好像必須承擔這樣的責任。現在我的兒子跟我的媳婦就住在我家的樓上,我每天看到他們工作也是非常的忙碌,要看小孩的功課,要在家裡教育他們,我感覺他們兩個人現在的工作,就跟我以前單親媽媽一樣忙,我很高興現在我已經是祖母了,我已經從教育小孩中畢業了。雖然父母親比以前更忙了,比較沒有時間教育小孩,但教育的標準卻提升了,這是因為全球化的過程,來自經濟的壓力,讓國家必須要提高教育的標準。大家也許聽過布希總統的政見:沒有一個小孩應該落單或是落後。但在此時也是發生教育補助被減少或是刪除的事實。這樣的情況會影響教育的品質,因此最近我們發現媒體會鼓勵把這樣的責任放在家庭教育不足的身上,甚至鼓勵有工作的母親變成在家的全職母親,能夠負擔這樣的教育責任。這樣的情況會帶給低所得家庭,或者是像我來自多倫多且有百分之五十是家庭收入不是很好的移民家庭的社區中,帶來更大的壓力。另外我要補充,在美國這樣的情況比加拿大嚴重,除了剛剛提到母職的論述之外,我們也必須考慮到教育的論述,但教育的論述有一些盲點,例如:以教育學者來說,母親的義務工作都不算是真正的工作。在我看到的教育局的建議中,他們會建議母親在家做一些教育訓練,例如一些繪畫的訓練,但這都沒考慮母親的時間或者財務的狀況,例如要有足夠的空間,要有錢去買這些材料,甚至要有時間來陪小孩或者教小孩這些繪畫的技巧。
假設說我們用上面的這條線代表教育,藍色的部分是媽媽在家裡做的工作,是一些看不到的工作,綠色代表老師在學校做的工作,我們可以試著去想想這樣的情況。而目前的問題是,現在的教育預設母親會做那些藍色部分的工作。但是我們可以想像是不是在未來,這整條線都是可以由學校來負責。
問題1:身為一個社會學家,你怎麼克服你自己所處社會的性別問題?
回答:回想三十年前開始社會學的研究工作時,的確有遇到困難,例如學校不願意開設女性議題的課程,但是現在全球有很多優秀的女性主義的社會學家,而這些問題已經漸漸改善了。
問題2:你認為課程的設計應該學生家庭的不同經濟地位做不同的安排嗎?
回答:舉一個在大學教書的朋友遇到的經驗,有兩班一起面對新課程的實施,其中一班的學生程度比較高,另一班比較低,但是課程的規劃是沒有彈性的,所以一段時間後,程度較低的班級的學生就會有許多人放棄學習。這是一個不易解決的問題,也必須繼續被討論。
問題3:你認為象徵女性社會角色轉變,使男女地位更加平等的里程碑為何?
回答:第一個是在1970年代,加拿大脫離英國殖民地時重新制憲,新憲法中有許多條例保障婦女權利。第二個是在1980年代後期,加拿大把一個墮胎的法律從法律中拿掉,把墮胎的決定權交回個人手中。這是我認為兩個重要的里程碑。
問題4:請您分享自己一邊照顧小孩,一邊得持續研究的經驗。
回答:我自己孩子小的時候,回家之後還是不斷地工作,一段時間後,當孩子不斷地成長,自己的學術成果也越來越顯著,論述也在累積當中。所以有時候必須靠時間解決這樣的問題。
問題5:如果我以後是個老師,你認為我應該要怎麼幫助單親家庭及低社經地位的學生?
回答:我想鼓勵未來的老師,在教育學生時,不要被傳統教育的論述限制住,把學生的問題都歸咎於家庭。記得自己有一次被小兒子史蒂芬的老師叫到學校,老師問史蒂芬是不是在家裡遇到什麼樣的問題,所以在學校才這麼不守規矩,小兒子說如果自己遵守規矩的話,在班上只能算是普通的學生,一定要靠自己不守規矩,才能受班上同學的歡迎。所以學生在學校的行為,可能是因為同學之間的互動而產生的,不一定要馬上歸咎到是家庭的問題。
問題6:如何改善社會的不公平教育?如何改善家庭教育?
回答:改善家庭教育工作是一個很大的議題,建議大家上網站搜尋資料。改善教育的不平等,台灣跟加拿大一樣,非常注重個人的平等,或許我們可以透過一些政策或政治上的互動,可以讓大家重視這個問題,再加以改善,也鼓勵未來的老師,能注意到班級當中一些不公平的現象。可以透過組織,例如教師會,來推動或讓大家注意到經費刪減的問題,或對其他教育的議題提出建議。
問題7:「如果人類處理紛爭的方式回到原始的情況--用武力解決,那麼未來權力將會重新回到男性的掌握之中」,你對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提出的論述有何看法?
回答:目前趨向於和平解決的趨勢,我不確定是否跟女性有關,因為很多女性也是會吵架的,但是這樣的趨勢的確讓女性更容易參與改變的過程。最近因為美國發動戰爭,可能讓大家感覺到權力又回到男性手中,但根據我的觀察,在過去幾年當中,兩性和平共處一直是各個國家的希望,所以戰爭並不可能把我們帶回到以男性為主流的情形。
問題8:加拿大是否也有類似台灣的安親班,為母親的教育工作減少負擔?如何減低母親的罪惡感?
回答:目前在加拿大也有類似的機構,但是當我的孩子小時當時並沒有安親班,我也同意安親班的確可以幫助母親減輕很多工作。我也鼓勵未來的媽媽不要以外在標準來衡量自己的表現,很多時候問題其實是出自學校,所以我們可以跟學校對談,讓學校瞭解我們的小孩在學校會有不受重視或負面的感覺,跟學校合作來解決這樣的問題。如果可以動員類似情形的學童和家長,跟學校一起進行對談,這樣的力量會比較大。
(二)、場次二:高雄師範大學(11/19/2004)上午9:30∼12: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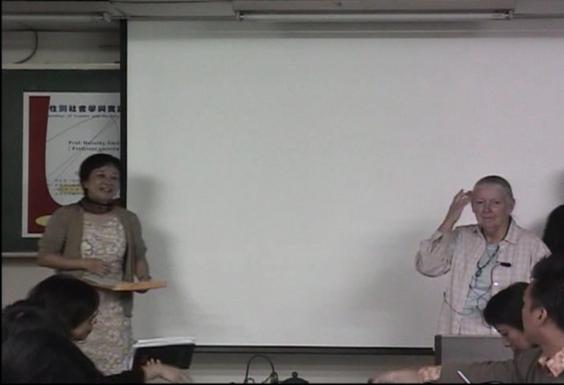
照片說明:
左邊為演講主持人性別教育研究所所長游美惠教授與Dr.
Dorothy Smit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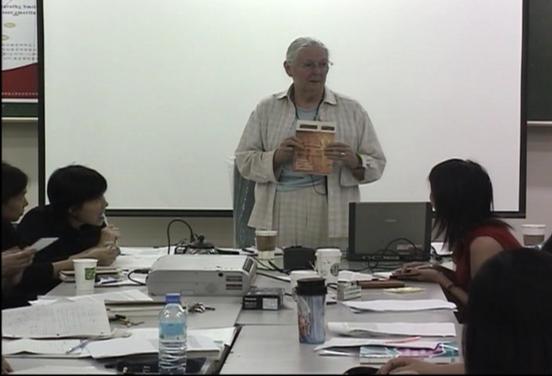
照片說明:
Dr. Dorothy Smith介紹她的「組織民族誌」相關書籍。左二為本演講中文口譯高師大性別教育所蔡麗玲教授。
演講內容:
身體所在的日常世界跟我在柏克萊大學所受的社會學訓練之間,我有一種失去連結的感覺。這個落差存在於女人經驗和我們參與其中的知識文化的論述之間。西方世界啟蒙運動追求自由解放,科學是解放的手段,意識藉著知識發展的理智而有所改變。我26歲念大學的時候,我以為我找到了自由解放;在大學裡,我發覺我所相信的是一個不被我的性別限制的心靈疆界。我當時並沒有察覺我正參與一個所謂的大學幻象,而這個幻象深深牽連著性別秩序。我念研究所的時候,這個落差尚未清楚成型,但是這的確在我後來參與婦女運動的時候指引了我提問的方向。
婦女運動轉換了我當年對於我所受的社會學訓練和實際生活經驗之間的落差。西歐國家一九七0年代早期的婦女運動中,女人開始討論身為女人的經驗,現在很難想起來當初女人是如何被排除與噤聲的,當時女人就是都沒有現身。我們當時有四個來自不同領域的女人教授婦女研究,那時候都還沒有相關議題的書。女人的聲音不被重視,女人的書寫不被看見、聽見;女人不能當詩人或哲學家,女人可以作個社會學家但是不能是理論家,當時每一個領域裡的要職都是男人。
早期的婦女運動,除了經驗沒有其他的依賴了,當時的論述都集中在男人經驗以及男人關心的議題,不容女人介入。我們只好站在外圍,從我們的身體開始,開始於我們身邊發生的事,那些沒有被說,不能被說出來的事。經驗的訴說讓我們得以創造一個新的論述,女性主義的論述。就是這些經驗的分享討論,就是這樣的激辯得以將這些經驗命名,進而組織起來,並賦予政治性的行動,在學習傾聽彼此的過程中,我們也學習如何爭辯、如何分歧,也就是在這些爭論分歧之中,女性主義理論得以成長茁壯。
經驗本身並非轉變的主因,真正讓我們轉變且成為女性主義論述發展基礎的,是對經驗的敘說,不是靠述說八卦,不是只能小聲地向朋友訴苦,而是尋找我們共同擁有的脈絡,然後將之公開命名,形成一種行動的基礎。經驗的敘說在婦女運動早期甚至沒有與父權論述對抗,反而是女人之間的一種探索發現,發現政治策略,發現真實,發現組織和行動的可能性;目的不全在改變論述,而是在父權實踐底下改變我們自己。
在我進行的社會學書寫中,女人可以是主宰探索的主體。在我過往的生命裡,我在家裡以及我在學術方面這兩者之間有個差距,在跟其他女人經驗分享的探索過程中,我學習到去探索我身為女人的自我,而不是只有在家當母親的自我,還有在無性別的智識虛幻世界裡的自我。看到我身為女人的自己,就是將自己具體化;將自己具體化,就是瞭解到知識生活的世界,不是只存在人們的腦中,而是在於人們每天日常生活的真實景況中。
傳統的社會學跟女人沒有關係,傳統的社會學是在生活之外所產生的抽象的知識,所以整個社會學的知識生產關係必須重新被建構。包括概念上的操作和實際方法上必須重新被建構出來,最重要的是必須跟我們的日常生活經驗連結在一起,必須從女人的立場出發,每天的經驗和生活中的真實性出發。可是如果我們來看每個人是自己生活經驗的專家,為什麼我們還需要社會學跟自己對話?因為我們需要了解這件事情是怎麼被組織起來的,所有我們生活學習的條件是如何被組織起來的;這些是我們在經驗之外應該被關注的東西,這是社會學應該關注的焦點,這也就是我說的為女人的利益產生的社會學。
這種組織狀態就是之後會提到的宰制關係,我們要注重所謂的真實,必須從每一天的生活開始。translocal指的是我的在地和你的在地之間跨區的關係,這種關係如何形成是社會學中重要的問題;我們跟其他區的生活經驗可以被結合在一起,新的社會學的目的就是要把我們這些真實的生活經驗發展出來。
我介紹的是組織民族誌,因為民族誌的方法是處理日常生活的方法,要找出統理日常生活經驗的模式,要加上制度。因為這跟一般的民族誌有些區別,最常見的跨區關係是經濟上的關係,例如7-11,這種跨區關係讓我們每天的生活得以順利。例如最近的新書講母職,原本我和朋友對單親媽媽和小孩子的關係開始,後來發現不是只有跟單親媽媽談而已,還要跟學校的行政人員和老師談,因為這些都是宰制關係的一部份。
後現代主義在歐洲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挑戰,馬克思主義沒有辦法處理一些社會上的現象。後現代主義認為沒有辦法用馬克思的後設論述來解釋所有的現象,應該要用語言遊戲來解釋一些概念,所有的故事或論述都應該要在各自的語言系統操作,因此再也沒有所謂統一化的認知主體或知識。後現代女性主義者強調,我們的生活被論述包圍出來,論述決定我們的認知或談論我們生活經驗的方式,沒有在論述之外的東西是不能被說的。我給大家講一個論述的例子,例如在加拿大有些學生用助學貸款上學,所以他們會想辦法早畢業,所以他們一個學期修很多課,同時要打工,但是這些因素完全沒有在評分的論述中被看見,所以機構的論述並沒有說出他們的經驗,這是一個反例。
後現代女性主義也不相信總體性的論述可以解釋一切,所有認知的主體都是斷裂的,由各種不同論述而形成的,也沒有任何一種方式可以決定最後總和起來的結果會是怎樣。我贊同後現代女性主義的一點,便是他們對論述的強調,對我而言是很有價值的,因為我想要討論的宰制關係是透過文本來呈現;但是我反對的他們的地方是,他們認為這樣子就沒有一種研究提問的方式是可信賴的,那麼做研究就不會得到發現,這是最大的問題所在。
我要講的組織民族誌,最重要的就是從人們的真實生活出發,我們如何“參與”跨區的組織關係。民族誌最重要的觀念,就是把研究者跟確實發生的事情連結在一起,若像後現代女性主義那樣的研究觀念,真相是再也沒辦法被說出來的。可是我們做研究的目的就是要告訴大家真相,但我認為的真相並不是不能被改變的,我現在研究的真相,是以現有的成果所呈現的;跟科學家不同的是,我們對於研究的經驗是很熟悉的,不像科學研究,科學家是在研究之外的,所以我們的研究成果是可信賴的,因為我們每一天的生活都會使用。
問題1:ruling
relation跟power
relation有何不同?
回答:我想創造女人的語言,power
relation給人無力感,不是每個人都可以運作自己的power
relation,例如我英國的學位到美國不可以抵用,這是因為有一個ruling
relation在那邊,並不是自己去運作power
relation就可以改變它。所以民族誌要從基層層次開始往上,希望能改變一些事情。
問題2:有沒有一些標準鑑定“精準的、可信的、可接近的、可使用的”等讓人們使用我們生產的知識的方法?
回答:知識要從特別的關懷出來,我的一個學生曾經關懷受暴女人,他們處理了一些跟受暴女人有關的法律;我的學生就用組織民族誌的方法透過911電話紀錄和警方的紀錄等文本,來探討這些法律對受暴女人有沒有幫助,因為警方的紀錄會決定案子能不能被呈上去。透過文本我們可以看到一些實證的故事,我們要去研究如何改變危險的程度,而最後的確有改變。
問題3:經驗似乎是真實的、不那麼政治的,但是人在描述生命經驗時必須透過語言來傳達,而語言本身卻帶有政治意涵,故我們該如何思考所謂的經驗?
回答:我舉一個非正式學習的經驗,在一個加拿大鋼鐵工廠中,他們有種非正式的學徒制,我在跟他們談的時候,就已經開啟了研究者想像中的世界,研究者要從別人的經驗中去學習。一個教學法的理論對我有所啟發,例如曾有一個員工受過傷,他便教導新來的工人,一遇到危險的時候馬上跑離現場,這就是從他自己的經驗中發展出來的非正式學習,而這是後現代女性主義者沒有辦法看到的部份。
問題4:人們會用不同的字彙、符號,來描述相同的情境;挑選不同字彙的人,不是在反映自己字彙的偏好,而是字彙本身連接到不同的社會想像和社會關係,當不同的語彙出現時,女性主義者要如何思考這種意義?
回答:妳問的東西是如何詮釋的問題,但這不是組織民族誌要解決的問題,也許妳可以看看警方的紀錄,和法律體系是如何定義性侵害和性交易的。
問題5:誰可以決定婦女政策的優先順序,特別是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性別主流化的議題是誰決定的?
回答:我認為不應該只有一個訴求,我舉加拿大女權運動的例子,一開始女權運動只處理墮胎權的問題,之後女權團體有一些不同的意見,分成了很多團體,在不同的機關部門努力,所以後來加拿大產生了西方世界最具自由主義的法案。到現在加拿大的團體和關注的議題已經很多了,所以我對需要優先被關注的議題沒有特別的建議,但是這些議題在30年後在這裡被發生,顯示透過教育的力量,很多東西是不斷被累積的。
問題6:資本主義讓女人的處境不堪,還是為女人創造機會?
回答:我一開始並不是要從抽象的理論層次思考,例如資本主義或父權,最重要的是要從事實來記錄實際上發生了什麼,尤其是馬克思主義所說的資本主義本來就是隨時在變化的,而我強調的是事情是怎麼被操作的。
問題7:有沒有一個社會關係是非機構式的,如果有的話,妳要怎麼去理解它?我們理解的社會是不是一個大鍋子裡面充滿了各種的機構?
回答:組織民族誌的意思,是指正在操作,有某種功能的重結聚合在一起,他們之間怎麼連結使事情可以被操作,例如高雄的醫院和台北的醫院不一樣,但是我們卻認得出來這是醫院。組織民族誌的三個重點就是:1.人永遠在那裡;2.他們正在做什麼;3.他們如何做這些。要從這三點開始做提問發現,組織民族誌不是一個方法論,是一種社會學,這跟我們傳統的社會學的分類不一樣。
(三)、場次三:台東大學(11/22/2004)上午10:10∼12:00

照片說明:右邊為主講人Dr.
Dorothy Smith,左邊主持人莊佩芬教授

照片說明:台東大學聽講的學生
我的研究夥伴和我都相當關注母職和學校之間如何連結,女性的母職如何成為學校生活的一部分?而當母職成為學校生活的一部分時,對學校生活會發生什麼影響?而在不同情況之下的母親和學校又會帶來什麼差異?因此我們試圖研究學校的例行生活如何透過家長所付出的心力和時間來運作。
在我們的觀察中,學校每天的生活由父母的工作開始,叫孩子起床、送她們上學等等。但是在許多家庭中,母親必須工作以獲得收入,因此她們能夠提供給兒童和學校無酬的協助變減少了,工作疲憊的母親無法早起送孩子上學,監督孩子的功課等等,使得工人階級居多的學區產生和中產階級的學區截然不同的問題。此外,全職工作的母親無法到學校擔任義工,在我們的研究中,我們觀察了一些在學校擔任事務性工作的義工家長,她們協助教師處理教學上的事務使教學活動更順利而豐富,她們的工作的確分擔了許多教師的日常工作,這樣的情況使得擁有較多家長支援的學校和缺乏家長支援的學校有了決定性的不同。
在我們的訪談當中,我們可以發現全職母親和職業婦女有著顯著的不同,其中,全職母親花許多時間陪伴孩子課餘的教育活動,使得他們的孩子有更高度的資訊刺激。但是職業婦女則無時間心力去負擔這樣子的活動。而這樣子的差異經常使得無法提供時間心力的職業婦女產生毫無理由的罪惡感,讓她們覺得她們是不稱職的母親。此外,許多關於母職的論述經常傾向於將孩子在學校的偏差行為或是表現不好指向於母親的過錯,諸如母親疏忽孩子的情緒變化、對孩子生活的參與不足、或者是其他的理由。這樣的論述也深化了母親和學校教育的關聯,而這樣的論述是由中產階級的全職母親典型而來的,也因此指責了其他無法完全投入於母職的女性。
我們可以觀察到,教育趨勢的轉變,,也使得女性的無酬勞動和學校教育產生更緊密的連結。由於教育預算的不斷減少,因此使得家長提供的無酬勞動的重要性不斷增加,學校越來越依賴家長所能提供的資源,因此使得享有大量家長提供資源的學校和缺乏家長奧援的學校在資源上有了顯著的差別,特別是公立學校在這樣的趨勢下所受到的影響是更大的。公立學校必須要在較少資源的情況下達到和私立學校一樣的教學水準,這當然是不可能的,因此公立學校的教學品質便逐漸和私立學校的教學品質、內容產生顯著的差異。我們必須要注意到一點,相對於父母親都需要去工作的勞動階級或是單親的家長,能夠提供足夠無酬勞動的家長在經濟上和時間上是較寬裕的。換言之,這樣子的體制轉變使得整個公立教育體系越來越偏向有利於中產階級家庭,而不利於經濟或社會地位較差的階級。對於原本就比較缺乏社會資本的社會族群,這樣子的體制無異是一種不公平的機制,而這個體制的運作便使得不公平的社會狀況一再的被重製。這也就是我所謂的,不公平的機制。
演講提問:
(1)
可不可以請Smith女士對台灣現下許多隔代教養的問題提出一些看法。
回應:隔代教養的問題是結構性的問題,但是我們可以看出來當這些孩子在學校遭遇問題時,論述的方式經常把問題的來源指向家庭,我認為這樣子的論述基本上並不太公平。
(2)作為一個社會學家應該要完全客觀於社會現象之外,以Smith的研究方式來說,不知道他會不會過分涉入於研究的現象之中,而失去其客觀性?
回應:因為每一個個體都存在於結構之中,每一個人的生命經驗和邏輯建構都會受到結構的影響,因此不可能有全然的客觀的研究。同時又因為我們的知識和邏輯思維是被建構出來的,因此有很多女性在男性父權為主的邏輯思為下根本就無法產生對結構的批判。布爾迪厄的訪談對象是以男性為主,透過其訪談的對象產生了他的理論,但是這樣子的理論是由男性建立的通則,但不能夠以男性的理性作為絕對的客觀。
(3)社會上存在許多不同的意識型態,這些意識型態間會彼此競爭,其中有些會成為主流,我們如何產生判斷力?另外,組織民族誌的研究法應該要怎麼進行呢?
回應:組織民族誌的研究法並沒有一定的模式,必須要視你研究的主題而定,你必須要先確定研究主題的特性才能夠決定研究的方式要如何進行。
(4)
我在學習社會學上感到挫折,因為我們似乎只能學習理論但卻很難應用於生活中,您可以給予一些意見嗎?
回應:我想多觀察、多閱讀是很重要的。透過觀察生活中的社會現象你比較容易開始將學習到的理論應用出來。
四、陽明大學(11/23/2004)下午1:30-3:30
陽明大學護理館613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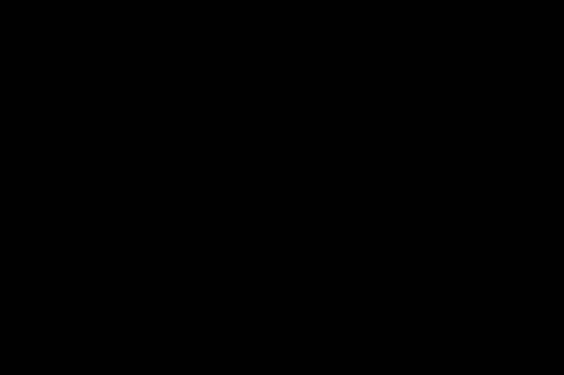
照片說明:左邊三為Dr.
Dorothy Smith與陽明大學場主持人陽明大學衛福所王增勇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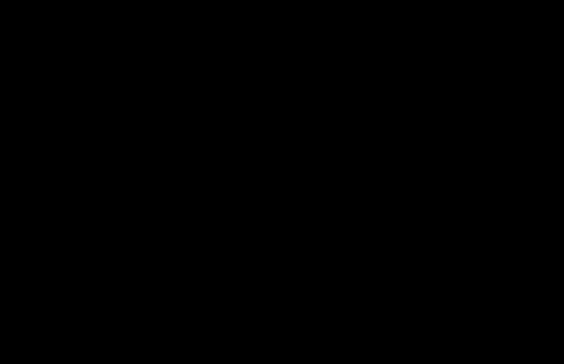
照片說明:陽明大學場主持人陽明大學衛福所王增勇教授與Dr.
Dorothy Smith
演講內容:
我一開始會介紹組織民族制的起源,尤其是在婦女運動跟社會學這兩個的起源,因為這牽扯到這個研究本身的性格,王教授已經跟我說,今天來的人有很多是在公共衛生這個領域工作,因為我還來不及找這方面有關的例子,不過我們會在最後來討論有關健康方面的例子,在七零年代,婦女運動的早期,學術界、文化界跟政治界都不太談論女性的觀點,而是以男性的觀點為主,我提出這樣的一個觀點,並不是要批評男性,而是要說這是一個歷史發展的結果,那事實上婦女跟男性都在尋找一個另類思考的觀點,所以我們這群婦女運動的工作者,正在尋找一種新的工作方法,讓我們彼此訴說彼此的經驗,來找出我們共同的基礎,而且可以命名我們的經驗,例如:我們就藉由英文的gender,“性別“這個字,用它來訴說我們的經驗,這樣的一個過程,我們希望可以命名我們的經驗,所以這經驗可以得到轉化,而不事去使用從男性觀點所發展出來的論述,社會學是一個沒有女性的一個社會學,社會學對於女人也沒有提供任何的貢獻,甚至於婦女所從事的工作在社會學裡也都消失,女人在社會學裡面如果想要說自己的經驗,就必須要透過一些抽象的理論,來偷偷的講一點自己的經驗,否則還沒地方可以說,所以其中的一個方法,就是在我們既有的世界之外,找到另一個位置,是我們可以站立的,把它稱為阿基米德原點,阿基米德原點的故事是說,如果我們可以在地球之外找到一個原點,那我們就可以用槓桿原理移動整個世界。
我原本以為我所經驗到的社會學跟斷裂,是一個社會學的問題,後來我發現原來不只是一個社會學的問題,事實上我就在生活上經驗這個斷裂,我在工作以外是單親母親有兩個小孩,但當我進入工作時,我的單親婦女的身份就消失了,如果女性要成為自己知識創造的主體,那麼社會學就要被重新塑造重新建構,因為在這種抽象化的概念裡面,其實很多的社會關係已經滲透進去,讓人成為知識的客體,所示這樣的一個知識生產關係要重新被組合,所以我們對知識的經驗必須要重人們的經驗為基礎發展出來,它必須要是一個為人民生產的社會學知識,而不是有關於人民的社會學,所以從人民的經驗出發,社會學家的目標是要去找出來到底我們身旁的這些社會關係是要如何操作,它操作的途徑是如何?要讓它能彰顯出來,這樣我們能找出我們的困境,這樣的困境是我們沒有辦法在我們每天的生活中都看得到,我當初提出現樣的一個想法時,在當時都被認為是不可思議的想法,所以我第一個想法是,每個人都是他生活的專家,以我自己來說,我在台北是一個外國人連標誌都看不懂,所以你們可以告訴我在台北要如何生存,就好像一個民族制的學者,進入今天的場域,可以跟我們說在這個場域裡的規則與組成,在這個場域是如何運作的,舉例來說教室地板如何被清潔,教室的燈光冷氣如何被保養,甚至於我們每個人出現在這裡,所有的這些都跟大學的運作有關,我們所存在的大學或是政府的組織,這些組織會把我們的工作跟別人的工作協調整合在一起,這樣的一個協調整合的機制,對大部分的人士看不見的。
所以我對於組織的定義是,組織是一種具有特殊功能的組成結構,例如是社會福利、醫院或是大學,但是這些組織其實都是相牽在很多的統治關係裡面,那麼什麼是統治關係呢?統治關係就好像我們生活裡面在遙遠南方的一座山邊,有一座山載等待著我們去探索去瞭解它的高度,那麼在我們生活裡面,都有一些很明確的關係在統治協調我們的生活,但我們對這些關係瞭解的很少,所以我把統治關係定議程一種被客觀化的意識,也就是它的呈現就好像我們機構所使用的文本或是圖像,這些文本的特性是可以重複的在不同的地方,被閱讀跟書寫被使用。所以我們在探索統治關係時,例如在街角的小店面,為何能以現在的面貌存在這世界上,所以組織民族制學者,他是從一個在地的位置利基點出發,來探索統治關係,而不是從抽象的理論是探索,所以組織民族制學是把我們生活裡的經驗,作為一個探索的經驗,把經驗問題化變成一個研究問題,從你的生活經驗去瞭解,我們生活經驗裡面,我們知道很少的這些統治關係,譬如:在7-11買東西時,就已經跟一群沒見過面的人發生了關係,但你卻從未察覺。所以這就是組織民族制學,一個從哪裡開始那裡結束的一個簡單的說法,我們去學習認識別人的生活,然後嘗試去瞭解他們的生活背後的統治關係,就好像學校教室地板髒了,我們只會瞭解清潔工不見了,但卻不會去瞭解學校雇用清潔工的方式流程為何?所以組織民族制是在探索,把我們跟別人連結的這些社會關係,到底是什麼?就好像一個地圖,有了這個地圖,我們就能瞭解我們跟別人的關係的連結是怎麼一回事。就像所有的民族制學一樣,組織民族制學藉由觀察、參與跟訪談,來學習人們怎麼過日子,瞭解他們的世界,但是組織民族制還要去瞭解,是什麼樣的關係可以跨越時間跨越空間,來把人組織在一起,所以我們用的名詞是,“跨在地“、“跨地方“
的來作這樣的組織工作。
我想在一步的去說明,文本跟統治之間的關係,在組織的流程裡面,如何在我們生活裡面觀察,文本所扮演的角色,舉例來說,一個警察到一個疑似有家暴的家庭,去家訪完後會寫一個結案報告,這個報告會把各種不同人的工作整合協調在一起,例如:檢察官、社會工作者、假釋官,他們的工作被整合,形成文本,就會形成所謂的文本真實,來認識這個家暴個案的情況,用文本的方式呈現,舉例:一個加拿大的社會工作教育者,她的書就是在寫在第一線社會工作者他們的民族制,他有一次紀錄了她的經驗,去一個疑似兒童虐待的案例裡,他在要進去前知道要寫一個報告,所他非常清楚知道他要看什麼,他才能把這個報告寫好,他一進去那個房子就看到一個十八個月的嬰兒躺在床上,所以他一去就很清楚的知道要把小孩抱起來,去看他的頭是不是扁平的,如果是扁平的代表他已經躺那邊很久沒有人照顧,所以作為一個訓練有素的社工人員,他非常清楚的知道自己要看什麼,而且這些東西會進入他的文本資料裡,但文本不會呈現的是,他對於那個原住民的母親所感到的遺憾,還有房間充滿的尿騷味,這些都也是他真實的經驗,但卻不會進入到他的文本,但她的報告會成為兒童虐待審判的重要依據。
另外一個例子,也是一個兒童保護的社會工作者,現在加拿大在引進一種新的兒童保護風險評估的流程,這個兒童保護風險評估的流程戲劇性的改變了社會工作者的實踐,因為這個兒童保護風險評估的流程是很精確,所以它不允許有錯誤,沒有太多的彈性,只是在關心是否要把小孩安置而已。社工人員不在關心這個家庭的狀況,例如:他是不是貧窮、是不是低收入戶,或者是不是新的移民,對養小孩方面有文化上有不同的文化觀點,或者因為他們是移民,正在經驗很多文化的壓力,這些都讓社工人員在這方面,無法在給他們這方面的協助,因為新的流程讓社工人員必須要專心把小孩作安置,不然在過去,這些空間是有的,社工人員可以幫助他們的家庭,申請社會救助,或是幫助他們就業,這些空間再新的風險評估裡都已經消失。
現在有一個護理教授跟她的學生在寫一本書,他們在比較八零年代中期的醫院,護士的工作處境,跟她的學生在描述現在醫院的處境,他在想說,過去的醫院每一個病房有穩定的人力,裡面的護士可以認識病人並跟他們建立好的關係,但在現在新的管理主義下,醫院設置的新的管理制度,每個病人進來被評估他所需要的照顧的程度,然後來決定這個病房需要多少工作人員,所以工作人員隨裡面病人的照顧需求而移動,所以他們現在正在記錄這樣一個工作環境的轉變,在他們現在的管理機制裡,護理人員也會參與,病人是否移動床位的決策,那麼他們現在也有正式的決策來決定病人是否應該出院,那其實卻不管他們家中是否有人可以照顧。
組織民族制統治關係就好像山群,就好像每個人都處於不同的起點來探索,每個人的探索角度不同,有的人在山腳下,有的在紮營,經由不同人的經驗,我們可以慢慢的對於山的高度跟形狀有初步的描述與瞭解。
所以在過去我們是屬於專業人員行政裁量權的空間,慢慢的在處於系統嚴密的監控下,所以這些組織民族制學發展出來的知識,我們發現在我們的專業理有共同的程序,正在發生在我們的專業裡,我可以想像在兩三年後,可以有一個國際的研討會,來探討在我們的專業裡發生了什麼事,也許我們可以來探討我們的處境,有一個更好的地圖來幫助我們瞭解。現在可以針對這方法來提問。
問題一:文本跟文本之間的差異是什麼?在演講裡用報告來代表文本,所以到底所謂的文本真實是指什麼?
答:其實每一個組織都有他建構事實特殊的方法,都有他特定的流程,每一個組織要看真實的東西也都不同,但是他們相同的是,一個組織要採去行動時,一定要透過文本生產出來的真理,才能決定她的行動,所以每一個組織都有針對它特殊需求生產出來的表格,因為每個組織要看的東西不同,也就是說他們要看真實的角度也不同,例如:一個警察要進行逮捕行動時,在她的報告裡一定要有正當的理由,才不會被起訴,最近在明尼蘇達的一位原住民婦女,研究在明尼蘇達的警察如何寫她的個案記錄,用一種方式所以家暴不會被起訴,例如:說男的酗酒,不會說他有家庭暴力的現象,所以有些事會被掩沒,只會凸顯一些事,所以文本真實的重要性,這些機構都有他特定的程序,來生產他們的文本,來呈現真實,所以他們可以按照這個真實來採取他們的行動。
問題二:那麼關於這些沒有被書寫,沒有被說出來的生活經驗那怎麼辦?那個不是才是反抗最重要的起源嗎?
答:對沒錯!這個就是我們對於官僚行政體系流程的最根本的批評,就是他們跟真實的生活脫節,這個可能就是生活的真實面,舉例來說,在剛剛講的原住民婦女的生活研究,許多原住民開始起來自己掌控法律的執行,他們就不要再重複過去的法律流程,才不會再犯過去的錯誤,原住民婦女的研究者,就在研究法律在執行的過程是怎麼樣傷害了婦女,所以當他把這個事情描述出來時,這樣的過程就有可能被看見,被提出來怎麼樣可以進行改善。在她的論文裡就更進一步的去倡導,改變了家暴警察他書寫報告的程序,譬如:夫妻分開偵訊,還有過去的受暴史必須報考慮,才能瞭解受暴婦女的處境,所以說作這樣的研究,鎖定的是幾個程序而不是針對個案上,關於這樣的一個組織民族制學的方法,最好的地方是我們是在記錄工作流程的細節,怎麼樣把所有的事情放在一起,所以當你記錄這些細節後你就可以提出一個可以說服人的說法,說明這些流程該如何改變。另外一個婦女學者,曾經做過一個研究在溫哥華那邊,研究一個身心障礙的診所,運作的中心是希望能夠以安全為中心的精神,他做的一個事是,瞭解案主想告訴你的是什麼,而不是去按照表格進行訪問,當按主要告你時,你不斷地打斷他,因為你只想知道表格上面的事,所以是在機構運作的流程上作一些改變,這樣的改變雖然很小,但在我們的範圍內所能作的改變。
問題三:要聆聽案主的心聲我很贊成,但這樣的方式非常的昂貴,所以我們沒有那麼多的人力來瞭解案主所告訴我們的那樣多的故事。
答:在做組織民族制學時,你收集資料有非常具體的焦點,你想要知道那個位置的人,生產那個文本的人,他腦袋裡的想法,你並沒有對那個人的身家調查有興趣,你只想知道他在那個位置上,他是怎麼樣操作,把那個工作做好,你是非常有焦點的去瞭解,他在那個位置上,他的知識是什麼?所以跟著那個流程,去瞭解那個流程上,在那些位置的人,他們的知識是什麼?所以組織民族制,有很清楚的問題焦點,但並不預設你能夠回答的內容是什麼,所以還是開放的。組織民族制可以有效率的收集資料,你可以邊走邊收集,收集來的資料可以在問下一個問題,我們其實可以知道,這世界是沒有界線相互連結的,所以在做研究問題時一定要設定一個特定的界線,在這些界線內才能有效率的收集資料,瞭解你需要怎麼樣的資料來回答你的問題。
問題四:可否解釋以女性主義的觀點進來時,讓我們看組織民族制時,會有什麼不同的觀點,一個好的衝擊出現?
答:不要從抽象的觀念來探索性別的關係,而是要從具體的,你在哪裡?你的關切是什麼?從具體的生活經驗來探索性別議題,回到自己,自己的經驗是什麼來發展。
問題五:大部分的學生比較關心,怎麼形成一個政策,一個政策會有組織在協調,但有些新的政策會成立新的組織,來做成政策,而有的政策會有很多不同的組織來參與,以前我們都只討論單一的組織的問題,可是這些組織如果併在一起,那要如何用組織民族制來將他變成一個習以為常的現象,應該有一些民族制的工作可以作,既然教授說這個方法這麼有用,能否告訴我們學生如何作?
答:公共政策如果以組織民族制來看的話,不是在看抽象的公共政策,,而是在看具體的文件,如何被閱讀如何被生產,在什麼樣情況下被書寫想產生什麼效果?如何被閱讀產生什麼樣的理解,之後會跟上什麼樣的行動。永遠要注意的兩件事,一個是文本,一個是跟文本相關的流程包含了哪些?文本並不是被動的在那邊被閱讀,他是在行動中積極主動地組織我們的生活,所以這些東西都可以去實證,去看被理解被運用的過程。
問題六:這個方法發展到現在是否一個很有效的對抗管理主義的方法,除此之外還有其她的可能性嗎?
答:做質性研究最重要的一個規則是,你只收集你需要的資料,不要收集過多的資料,作為一個局內人,用組織民族制是一個優點,也就是說你其實已經知道很多內部的消息,所你很快的就可以知道,那個關鍵點在什麼地方,且局內人所擁有的知識不僅僅是主觀的經驗而已,事實上他們也會對自己所擁有的知識感到驚訝,舉例來說,曾經做過鋼鐵工人的訪問,那些工人一開始說自己什麼都不知道,但訪問兩個小時後,發覺他們其實對自己的工作有很多東西要說,而且他們也真正有去思考過,他們在工作上面所發展的知識,而且他們去教育別的工人怎麼樣作這樣的一個工作,有些工人不只談他們的工作,還說這樣的工作對他們的生命,對他們的生活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跟意涵,所以做為一個局內人,正好是做組織民族制的一個很好的起點,而不是一個缺陷。在理很重要的一個區別是,只要花你時間花你精力的都算是工作,並不是有領薪水的才叫工作,所以回到之前的問題,你在那個位置上,你有很多的知識,所以你的那個知識是你做組織民族制學一個重要的資源,只是你還需要去瞭解別人的工作經驗,作為擴展你自己組織分析的一個架構。舉例來說,在安大略省西南鄉村地方,有一個計畫請我當顧問,在那個計畫裡,那個區域有很多有三個婦女團體,因為那裡婦女的貧窮率跟失業率很高,這三個婦女想要幫助那裡的婦女改善他們的環境,所以他們會跟那裡的鄉公所一起合作,開始討論如何改善那裡的環境,他們要用的就是組織民族制學,來瞭解他們現在那裡所面對的具體問題,所以不光只是對抗管理主義,他也可以是從不同的脈絡有不同的關切點,雖然我發明了這個方法,我也做了大部分的理論的工作,但很多創新的是我的學生,可能你關心的這個管理主義的部分,可能有一些我的學生,他們比較有能力來回答你的問題,明年也會有一些這方面的書出版,看到自己學生青出於藍,我也感到很高興。
問題七:從組織民族制可以聽到一些系統裡最沒有權勢人的聲音,再從最沒有權勢的人出發,去改變系統,但在真實的世界裡,這些最沒權勢的人對於改變系統是最無力的,對於這些洗統裡不同位置的人,它們之間彼此擁有權力跟利益關係,會不會對於這些人來說,這些經驗的出發反而是造成更無力的來源?
答:組織民族制學,他所生產出來的知識,不見得能做出什麼改變,但是這樣的知識是有用的,它可以用在幫助機構把它現在做的是,能夠做得更好,組織民族制也常跟一些倡導者工作來瞭解系統,它可以不同的用法,所以它是一種知識生產的方式。
四、台灣大學(11/24/2004)下午3:00∼5: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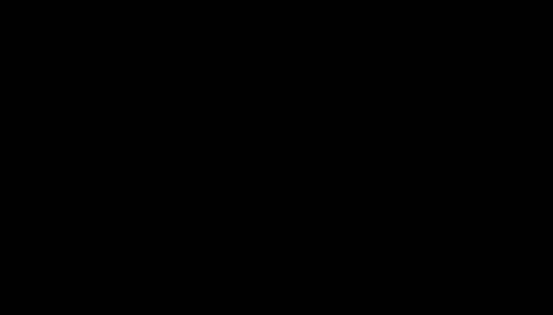
演講內容整理者:程雅欣
主持人:我們很感謝Dorothy在忙碌的安排中撥空來到台灣為我們演講。我們許多人,多年來都受到Dorothy的啟發。身為一位女性主義學者,尤其又是社會學家,Dorothy致力於發展一套女性主義社會學,並且建造了一個別於標準典範的社會學。我引一段Dorothy書中的話,社會學是一種系統性發展的社會意識,還有社會關係意識(sociology
is a systematically developed consciousness of society and social relation)。我認為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需要一種不一樣的社會學—我們渴望不一樣的社會關係。而Dorothy對這的努力更激發我們加入他的行列,建造一種不一樣的社會學思維,造福所有的人。現在就要請Dorothy來為我們介紹一個女性主義社會學。
Dorothy:能夠受邀請在這裡做演講令我很高興,首先我要做一點背景介紹,說明我如何決定要發展一套不一樣的,為女人做的社會學。因為這一切都跟我的個人在女性運動裡的經驗非常有關係。另一方面,我也要提醒大家這種個人性的關連。因為他發展起來時,這些關連性就常常被淹沒,消失了。所以現在我要重建這個關連。
在西方的啟蒙時代開始了很大的風潮,人們認為理性和理性的科學知識允諾了自由(liberation)。而在北美,這個風潮不只是思想的運動,他實際上變成組織制度,而且是由男人主導控制的各種組織。是這樣的歷史過程形加拿大跟美國後來的樣子。我進大學以前當過秘書,那時候我跟知識啟蒙(the
light of intellect)沒有什麼直接關連。所以我踏入大學殿堂時,就愛上啟蒙了。我以為自己找到一種美好的信心,以為知識啟蒙可以減低消除我曾經驗過的女性的壓迫。但事實卻是,我的學術生活跟我身為女性每天在社會中的生活,有個斷裂分離。研究所時我在加州唸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n Berkley)。去過的人可能知道他的校園充塞著建築物,不過當時那裡有蠻多樹啊,草地,還有小溪穿過。我常常走在校園裡思考這個斷裂:社會學式的世界,我所受的學術訓練,創造著想像中的世界。我對這個斷裂感到很焦急,社會學可以討論的東西以及我身處的世界之間,有個鴻溝。
後來女性運動非常急速地興起,現在大概很難想像當時怎樣,或者連六七0年代早期的情形都很難想像。我們沒有女性意識,根本連可以討論我們自己的語言都沒有。像是我們現在常用的詞彙:性別(gender),父權制度,性別歧視(sexism),或是受到性騷擾時要怎麼講出來。我們沒有語言,無法公開地用正當的方式討論自己,我們根本不存在。於是,我們著手進行很基本的實踐。這是個政治的實踐,跟選舉那種政治不一樣,但它關係到權力,如何使我們自己變得有力量。必須要開始談論自己,從自己所站的位置觀點出發。這些是必須做的改變。我們透過彼此談話,講自己的經驗來達到那個改變。重視個人的經驗,在後現代女性主義論述裡尤其重要。個人經驗不只是關乎個人層次,他可以重塑我們,重塑我們的關係,成為政治動員的基礎。我們一直談個人經驗,用對話的方式(dialogic)彼此交換,且永遠都會有新發現。我們因此看到別人有我們未曾想像過的經驗,發現自己從來不知道有這種東西可以學習,不知道存在這種事情。所以說,在我的作品中,跟別人講話,談話,成為很基礎、重要的東西,一種方法(method)。
當我採取這種方法及觀點時,我來看社會學就發現許多問題。身為女人,擁有女性身體,有小孩,家務工作,以及許多在地的特殊性,我在社會學裡,除了一些遙遠的聲音以外,找不到有關自己的論述。鴻溝就在這裡,我念研究所時感覺到的東西又回來了,它不是一種外在的論述,而是在我裡面。於是我開始想到,從我們生活的女性身體、在地的特殊性為立基,建立一種女性的社會學,會是什麼樣子。我開始想像社會學研究各個特殊的地域(local
particularities),比如我們現在所在的地方,或者別的女性研究所處的場所。這種社會學有一種真實(reality),不只存在於我們的腦袋裡,而是存在於人們的實作,以及各個實作如何協調。要有這種社會學,就必須有不同的方法,因為我學過的社會學,我所受的訓練都阻礙了人們研究個人經驗。所以我無法採用社會學原來的方法。我所學的社會學不太談論女性,通常對女性議題沒什麼話好講;就連談論家庭的(的確有談到女性)部分也對女性著墨甚少,而且完全不把女性在家裡所做的事看成工作。我記得我完成博士研究後,去找指導教授,說我真正想研究的是家庭裡的工作,女人做的工作(household
work, and work that women do in the home)。他回答說:親愛的,你必須為自己的人生規劃著想(career),別這樣做。社會學也沒有談論個人的經驗的空間,更不用說女性的個人經驗。不過我認為這情形在最近十幾年已經大為改善了,不過當年,你必須偷偷把經驗藏匿在社會學研究裡。我記得當時有個人想要從一個社會學家的角度談事情,但他必須想出個很巧妙的方式。他不可能直接站在自己的立足點上,說我認為這就是我要研究的,說這很有得研究;你就是不能這樣做。或許現在可以這樣做了,這方面你們可以提供我知道,因為我大部分時候並沒有跟社會學連得很緊(但我應該是要有所聯繫),我太忙了。
以下是我遭遇的的問題之一(例子有很多,這只是一個),我在大學裡指導參與過女性運動的年輕女性做研究,他們想要做有直接政治性的研究,所以就打算研究女性運動,並理所當然地使用社會學的社會運動理論。但是對我來說,這樣很奇怪,變成說,你原本是真正參與其中的,但在研究裡卻變成一個客體(object)。而且誰有興趣知道社會運動裡面的女性運動?也許FBI有興趣吧…?,但對女性來說,他沒有什麼用處。這種研究完全沒有說出女性運動裡頭有用的東西。這種被困在社會學的情形,像是陷在一個自己會運轉的機器裡。這導致即使你有特定的政治目的(談論女性,使女性有所助益),你仍然無法一邊做社會學研究,一邊遵循原來的意圖、邏輯。這就是必須改變的東西。
我們被社會學的概念性方法困住,作為一種方法(methodology),社會學把人們以及他們所做的事情變成研究的客體。所以,身為一個社會學者,在研究中是主體,但所做的研究卻會落在他的生活經驗之外。我認為這根本不可能做到,不過在文本裡(in
the text)卻實現了,使用很巧妙的概念性技巧,他在文本裡就是這樣。這就是我極力想避免的事。我要創造一種社會學,從人的生活跟經驗出發,所以需要設計出不同的方法來研究。要改變就必須想出另一種研究方法。光是改變政治意圖無法達到什麼真的改變。我個人覺得,甚至打開門接受個人經驗,也不足夠(雖然這個改變對社會學很好很重要)。我覺得那些都不夠。我想要的社會學,其知識來源是人的經驗,社會學知識必須固定在個人經驗之上。這樣的社會學會告訴你,你周遭的事物如何連結在一起;他不是把你變成客體,你會成為社會學的主體。
我開始時跟馬克斯學習,他對我很重要,卻不是一般重視馬克斯的那些原因像是馬克斯主義。他對我很重要是因為,我看到一個社會學家可以怎麼著手進行研究。不要從理論、概念、沈思、想像開始,而要從人們實際所做的事,進行的活動,還有進行這些活動所需要的條件(condition)出發。從馬克斯開始,我又從女性運動學習到別的東西。馬克斯不會加入女性運動,即使他生在那個年代。馬克斯沒有看到立基於身體的經驗。我受到馬克斯以及女性運動啟發,所做出的社會學,現在叫做組織民族誌(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這種社會學不是從理論出發,而是從一連串的個人提問出發。問的問題是:各種東西怎麼組合起來,人們怎麼把這個與那個連結起來?這個社會學不使用預先存在的理論,預先設計的框架或概念來詮釋、評論社會。我用民族誌(ethnography)這個字是因為,實際上研究所做的事是找尋人們到底在做什麼,還有他們對自己的生活有什麼可以談論的。這在民族誌裡或許只佔很小的一部份,但我要強調的是,我們要重視人們日常生活中實際作的事情。所以概念是從這種研究裡找出來的,我們要從人們身上學東西。
人們是她們自己生活實作的專家(expert
practitioners)。我們對於自己的活動都是專家,比如說你知道要怎麼來學校,從家裡到學校該怎麼走,知道廁所在哪裡。而我就完全不知到這些,因為我不是你們生活的世界裡的專家。關於這些,要由你來告訴我。我也以組織民族誌做過大學裡的廁所的研究,但你還是有東西可以教我。這樣子從人們身上學習的過程,是組織民族誌的核心。
另一方面,既然每個人都是生活實作的專家,為什麼還要我來作研究,然後告訴你你已經知道的事情?這是因為我們的日常生活不是獨立的(self
contained)。人們可以用不同的方法來研究,記錄人們談話的順序,對話的模式。觀察時有什麼就紀錄下來。這些就成為他們的資料(data)。在日常生活的世界裡,真實的世界裡,社會關係不是獨立存在的(self
contained)。真實生活連結了各種關係,把我們跟遙遠的,做著不同工作的人們也掛上鉤。像現在這裡有看不見的存在,這些東西就會是組織民族誌研究的東西。我們向旁邊看看,地板清理乾淨了,有電燈,有空調,椅子都排整齊了,設備也都順利運轉。有次我在別處,清潔系統出了問題,地上的垃圾就整個堆起來,教室到處都是垃圾。各種事情都整合得很好,成為我們進行這個座談所必須的條件(condition)。我讀過一本很棒的書,關於口述歷史,是一九一零年代初期,書中描述這一群人試圖不靠電力生活,沒有電燈沒有電力。冬天的時候,他們集會的場所有個冰柱。我不知道他們進行智識討論時順不順利,不過如果有空調或暖氣,這樣的座談會一定會比較容易進行。這些面向在我每一天的知識圈的世界裡,在這裡,在大學裡;這整個場景,由某個組織支撐著,但我們平常卻不會想到它。我們不會注意到他,但他確實存在在此處。這樣的組織運作是大學的一部份,讓我們得以進行各種知識活動,就像現在一樣。我們不必時時憂慮會不會有霜結凍等等。這些就是組織民族誌會強調的東西,他會進入那個點,或者交叉點,在我們每天熟悉的生活中,這種組織制度協調各個社會關係,協調我們進行的各種活動。我們現在所處的地方,這個環境,與別人的工作(在別處或他時進行的),息息相關。我們對她們的工作不清楚,不瞭解,但他們做的事卻對我們很重要。甚至這些協調整合的組織制度會型塑我們在這裡(local
places)所做的事,我們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都取決於它。
馬克斯教我們怎麼看到了錢和商品交換的客體關係(objectified
relations)。這種特殊歷史條件下的形式,這特殊的形式關係,他稱作抽象(abstract)。一般人常常誤會他所謂的抽象,以為他在講一種概念的東西。但他是在講真實的關係,錢跟商品交換的形式,型塑的人們的關係,使他們的關係變成抽象(abstract)的關係。這種關係使人看不到另一端的人,比如去吃晚餐時。這種組織形式叫做客體,或是抽象。不過他寫東西時,我們現在這種組織制度還沒有出現,現在這種客體化的組織。他客體化了意識和協調過程。我們變成協調整和關係裡的主體和行動者,我們的活動跟他人的活動互相協調著。而所謂組織民族誌的組織,指的是相嵌在統治關係(ruling
relation)裡運作的綜合體,比如各個層級的學校、醫院、健康組織、政府、法律組織等等。他們也跟各種不同的關係掛上鉤。
這些統治關係和相嵌其中的綜合組織依靠文本和文本設備。我可能沒有什麼時間談太多,但他是個非常重要的面向。無論如何,這使得他們可以把不同時間,各個在地的語言或圖像複製起來。透過這個過程,他們可以管理組織在遠地的人,可以把工作流程標準化,計算利益獲損失。想一下社會學研究是怎麼進行的?有個部分,你需要有文本,可以在一個地方一間教室裡頭閱讀,但在另個地方其他人也可以閱讀。而這裡和那裡的人,這些和那些人,讀了同樣文本,其思考就會受到同樣的影響。不是說他們都會有一樣的想法,或讀出一樣的東西,但是這的確代表,有個整合的組織以一個既存的文本的形式,型塑他們。這些組織存在的方式的關鍵就在於這種複製。沒有文本,這些組織就不存在。你會越來越發現文本的存在,圖像的複製,比如電視。過兩個禮拜你們要選舉,或許你看著選舉的電視節目,你跟很多不認識的人,一起看到的一樣的圖像。這是我們這個世界的特殊之處,這使得我們的生活跟三百年前的人,差距十萬八千里。而大學組織就靠這種運作方式存在:一堆文本,到處都是文本。我們一直填表格,寫報告,做一大堆事都脫離不了文本。你寫好研究,拿去發表,不同地方發表會有不同的點數,然後就可以計算你考績,然後你終於知道自己的價值,知道你在世界上站了什麼位置。像這樣,組織制度運作有一些方式,標準化的流程非常仰賴文本,需要電腦化。嗯,我自己還沒有寫作過關於電腦化重要性的研究,只有在一些研究中零星談到電腦化的很小部分。不過繼續這樣的研究應該會相當有趣。我來舉個例子,說明什麼樣的文本,什麼樣的統治關係,滲透到我們每天的生活中。
這是我個人的故事,也是個人研究的故事。Alison跟我是單親家長,我們會聊到一些小孩在學校的問題,因為只要小孩在學校出什麼事,我們就會被指責是罪魁禍首。很自動地,只要你是單親家長,你的小孩在學校闖禍,則問題來源一定是這個不正常的家庭所帶來的影響。他不管你在家裡到底是否作錯了什麼,或者有沒有什麼焦慮壓力,通通都不管。單親家庭如我,就是會被指責。我有個有趣的經驗,我的老么在學校闖禍,我去教室裡跟老師談,我兒子也在場。老師就開始一般的詢問,問家裡發生了什麼事等等。Steve在後面也聽到這些談話,他就過來說,別傻了,我違反規定是因為我是班上的邊緣人物,我想進入班上的核心圈子,不作些違反規定的事,就沒法打進他們的圈子。於是Alison跟我就在想,學校為什麼這麼需要,這麼重視正常家庭,還有家庭中的家長?我們感興趣的不是家庭教育跟學校成就的關係,我們想要知道的是,到底女人在家庭裡做了哪些工作,使得學校這麼需要家長,並且這麼極力避免單親或不完美的家長出現在學校範疇內。那我們實際上做的就是訪問家中有小學小孩的正常家庭的家長,看看她們為學校裡的小孩作了些什麼。在這個過程中,統治關係以一種我們沒有預見的方式出現。有一天Alison很生氣地回來,他訪談了一位媽媽。那個媽媽擁有一切他所沒有的資源,他跟一個教授結婚,沒有在家庭以外工作,並且在家裡進行很多教育小孩的工作。他說了一件事,或許有點誇張炫耀,而且我猜這是為什麼訪談會令Alison狂怒。那位媽媽詢問小孩,要觀賞莎士比亞的哪一齣戲(這些小孩只有國小喔!七、八歲),因為附近有莎士比亞節,辦了很多活動。Alison因此感到被指控,感到愧疚,因為他沒辦法這樣做。他領福利金,沒有時間也沒有錢做這種事,不能詢問自己小孩要看哪一齣莎劇。
但是我們從女性運動學到,不要直接就這樣接受這些經驗感受。我們持續地談論,後來發現當時持續增加的女性主義者寫的歷史。那些研究當時突然如雨後春筍,大量出現在公共領域,很棒的研究。我們從這裡知道所謂的母職論述。這是個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出現的新發明,與當時北美的公眾教育系統有關,他動員、訓練母親們致力於小孩在學校的教育,幫助小孩更專注於學校的學習。這其實是個中產階級的女性社會運動,他們給大學壓力,要作兒童發展學,兒童心理學等的研究。不過當然,真正負責這些教育計畫的人都是男人。
這個論述中很重要的一點是,小孩如果在學校表現不好,媽媽就必須負責。非常奇特地,其他東西都完全不重要,這跟我們的經驗完全符合。學校的因素都不列入考慮,都不重要。小孩在學校出事,第一時間被指責的,一定就是單親媽媽,很理所當然,認為因為你單親所以才會發生這些事。有很多理論教你要怎麼改善小孩在學校出問題的情形,他們建議你遇到這種事要怎麼處理,但家庭其他的情形卻沒有放入考慮,比如收入。完全不會提到家庭的經濟狀況。你會看到教育部印製宣導手冊,上面告訴媽媽應該要跟小孩進行哪些活動。比如說,他會建議你有一塊空間讓小孩畫畫,準備各種顏料,筆刷,使小孩在這裡隨便畫。你可以想像這是需要資源的,錢不要說,畫畫會產生怎樣的凌亂,有多難收拾?而且你要有某種地板,某種樣子的空間才可以進行。但這些都在宣導手冊裡不重要。另一個例子是,你可以在家裡作一個舞台,然後跟小孩在那裡演舞台劇等等。這些建議裡都沒有提到經費,更重要的是,沒有提到需要付出多少時間。這些都是女人在做的無償工作。女人付出的時間不被看到,從來不被當作一回事。而Alison跟我都讀過這種文本,小孩出生後我們都念這些,他會告訴我們養育小孩該做些什麼事。這些論述到處都是,女性雜誌裡等等。他說你對小孩負有哪些責任,而實際上我們應該負全責。所以我們知道如果我們沒有作這些事情,就應該被指責,就應該感到愧疚。
這裡我們就看到文本論述是如何標準化這些主體。我們不是唯一閱讀這些母職論述文本的女人,或許整個北美的中上階級女人都在閱讀這些文本。Alison跟我,帶著我們做的研究,在北美隨處跟女人聊天,談我們的研究。其中有一次的討論,聽眾不完全是學術的人,有三個女人的回應很有趣。他們三個都有就讀同一所學校的孩子(我想他們不是單親媽媽),他們跟小孩相處都有問題,但是他們無法彼此討論談他們的問題。因為這麼做就代表自己必定是做錯了什麼。但一旦聽我們分享母職論述之後,他們就發現可以以此討論這些問題,而且可以去學校問學校的人說,你們到底在搞什麼鬼?像這樣,我們的討論有這種效果,可以變成那樣,實在不錯。更廣泛的影響,我覺得是可以看到文本怎麼動員女人,使大家在家裡從事沒有薪水的、而且內容相同的工作。有很多可以進行的活動,有些跟小孩玩的遊戲,來讓小孩的教育更順利優秀。這個論述現在已經更為精緻了,我小孩還小的時候還沒像這樣。而這個就是學校組織的特色,他整合內化了這種女人動員。學校有部分就依賴這些女人的工作。我們作的研究正是想尋找學校到底為什麼如此依賴正常家庭的家長,還有當家長沒有作這些工作時要怎麼辦:這樣一來學校就不能這原來的方式運作下去,而學校的工作人員對此很清楚。
發現學校組織的母職論述讓我們對於先前的感受比較安適,但對於改變這個預先存在於研究裡的預設,卻沒有抵抗能力。不過幸好我們做的是民族誌的研究,而非嚴謹的架構分明的調查,所以還不至於太糟。但我們在過程中學到很多,而這是很重要的部分。光是發現事情怎麼連結在一起,就可以幫助我們揭露、撼動原本當成是理所當然的事,這些我們以為我們早就熟知瞭解的事。從這裡我們就可以看到,在我們的實際生活中,各種關係怎麼組合整合在一起。我們生活在這些層層掛勾的關係中卻不見得自知。而這些關係會型塑我們的生活。以上只是一個例子,說明我們生活的世界裡,各種關係怎麼以我們看不見的方式互相連結。我們的研究也跟別人的研究互相關連。
這些統治關係構成了我們的真實生活,組織民族誌就是因此把日常生活看做有問題的,要研究這個。這樣的研究不把人們變成客體,而是延伸人們的經驗,連結到非在地的關係,看這些關係如何型塑我們的生活。
以下是個簡短的導引:組織民族誌從人的經驗出發,學習他們所知道的知識,以及他們對所參與其中的組織有什麼瞭解(人們通常要開始談論,才會知道自己其實知道很多)。這也是做組織民族誌很奇妙的事情。我有個研究,要訪問鋼鐵工人,他們一開始都會說,沒什麼好說的啊,我也不知道什麼。但一旦開始講話,我問他們是怎麼從別的工人身上學習到工作內容和其他細節。漸漸地,他們會開始講他們工作的世界是怎麼一回事。他們其實知道得很多,後來我還得煩惱怎麼讓他們停止不要再講下去了。他們變得興致勃勃,很多東西要講,因為這是他們有生以來第一次有人對他們的工作內容有興趣,他們有機會談論自己的工作。這個過程非常有趣又充滿驚喜。這會改變先前對工作過程的觀念和看法。他們甚至有一套教學法,他們會思考要如何教導後進的工人。有一個工人遭遇過很慘的工作意外,機器出問題,他想要把機器停下來,結果受到很嚴重的灼傷。他回家後,太太跟家人說他很笨,幹嘛那樣做?他這個人比工作更重要啊!所以他因此學到新東西,和以前不同的看法,並且把所學的傳承給新進人員。他會向年輕的工人說,如果你覺得不對勁,害怕,感到危險,就快跑,離開現場。其他事可以之後再討論,但當下趕快離開。像這樣,學到新東西,有不同看法,別於一開始作研究時的想法,就是作組織民族誌會有的很奇妙的事情。
從已經知道的開始,然後一步步探索連結在一起的關係;所以問的問題不會預先都想好,他會隨時著研究的階段而改變,這就是組織民族誌很典型的進行方式。你問不同人的問題,不見得會一樣。你可能會想要問同樣主題的問題,但是也可能你從前一次的訪談中學到新東西,所以下一個人就可以問更進一步的問題。隨著時間,你會問越來越深入的問題。
組織依賴文本,而組織民族誌就把關鍵的、整合組織的關係的文本揪出來,放到民族誌的眼光裡頭去。我覺得這是我們目前為止作的最基進的事情。我們看待文本不是當作靜止的,他告訴你該怎麼怎麼做;文本其實是主動參與的。比如你在圖書館裡頭看書,一邊作筆記,或者用網路搜尋東西。文本協調著人們的活動,這是組織民族誌很重要的東西。因為從文本你看到組織扮演的角色,看到組織之所以為組織的原因。
再來是它的影響,我想要強調的是,組織民族誌研究可以拓展人們對日常生活的瞭解,就像是一塊區域的地圖一樣,幫助看到原來看不到的東西。可以看到組織裡頭的東西,是什麼在左右我們的實際生活。雖然研究過程需要一些技巧,但做好之後可以再轉譯成日常生活語言,就像製圖學,需要一些技術,但他可以做出一張人人可使用的地圖,讓我們找到一條路,路跟路的關係如何,城市跟城市等等,
怎麼從這裡到達那裡。你不需要成為製圖專家,就可以看懂一張地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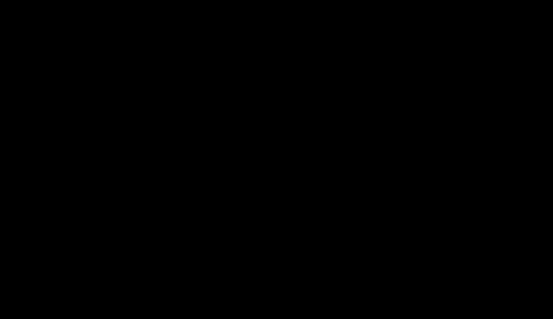
照片說明:Dr. Dorothy
Smith
演講後與主持人台大社會系曾嬿芬教授、藍佩嘉教授、吳嘉苓教授(依序為左四、三、二)等人合影。
主持人:接下來問問題,一問一答。可以用中文問問題,請王教授幫忙翻譯,想用英文問也很歡迎。任何問題都可以提。
問一:我的問題是想請Dorothy評論、比較一下組織民族誌和紮根理論(grounded
theory)。因為同學們上課會上到紮根理論,他同樣也是強調人的經驗,從那裡出發。但是我認為組織民族制的很重要的區辨是,他強調你要在微觀的東西裡頭看到巨觀,強調制度性的相嵌(structural
embeddedness),要看到統治關係怎麼運作。而紮根理論則強調不要有任何先制的理論預設,要bottom
up,從下面紮根,然後長起來。我想請問Dorothy的是,組織民族制的理論立場(theory
position)是什麼?特別是相對於紮根理論而言。
答:我對紮根理論最近的發展不是清楚,只知道比較早期的主張。我認為紮根理論和組織民族誌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不能拿來比較。組織民族誌學觀察的是人真實生活理發生得是,還有人跟人東西跟東西怎麼組織協調整合在一起。而紮根理論是社會學者系統性地觀察一個現象,再發展出詮釋。組織民族誌是從每個人的世界出發,看看有什麼新東西,事情是怎麼組織起來的。馬克斯有個期刊叫《Social
Thought》,他在談社會關係時,強調真實生活中的事情,從這裡面作政治經濟的考察。舉個實際的組織民族誌研究可能會比較清楚:Susan
Turner做過一個關於都市開發的組織民族誌學研究,他們要在山谷裡作開發,Susan嘗試去抗議,卻失敗。於是她作這個研究,把都市發展的決策過程做成一張圖表,列出各個流程。而環保人士從這個流成就可以看到他們介入的可能,或許是法律修正,或許是行政流程的修正。
問二:組織民族誌讀的來源(origin)是什麼?這種研究方法為什麼特別可以研究女性?為什麼他可以研究女性,又可以推廣到研究所有人?研究女性,在方法上有沒有什麼特別之處?
答:這個方法是我創造的,沒有其他來源。我有一些優秀的學生,現在在北美的大學任教,每年會有組織民族誌國際研討會,學生已經到第三代了。這個方法被應用在很多不同的助人專業上,包括護理,社會工作,都市計畫,社會運動團體…都在使用。
這個方法不只針對性別。可以讓不同的人使用。通常從特定情形下的問題開始,我舉兩個例子。Allan
Pam作的婦女團體研究,這個婦女團體支持家暴婦女,使他們能度過司法流程。他們採用組織民族誌來研究司法流程裡頭,婦女的安全如何被忽視。透過這個研究可以提出改變的訴求,在文本上也作改變。比如把丈夫和妻子分開來偵訊,分別完成偵訊報告,這樣的司法流程上的修改。但是組織民族誌也可以被政府採納使用,加拿大一個婦女團體跟當地鄉公所合作,想改善在低收入戶和失業率很高的地方,那邊鄉村婦女的情況。可能明年就會開始會進行研究,希望在流程中看到可以怎麼改善這種情形。
為什麼組織民族誌可以當是一般人的社會學?所謂人,不是一般社會大眾,而是真實的人,真實的人的經驗。從這裡開始社會學的研究。
問三:接著前一個問題,我想特別問,從為女人存在的社會學,到為人存在的社會學,這是什麼樣的轉變?
答:這沒有什麼很大的轉變,我在發展為女人發言的社會學時,必須作社會學研究上的概念轉變。之後我就發現這個沒什麼道理只能為女人發言,他也可以研究所有人,尤其各種被邊緣化的人可以透過這個方法作知識生產。
Dorothy問:王教授以男性身份作研究,如何看待組織民族誌?
王答:你不願意邊緣化研究對象,你真的關心研究對象,關心社會正義,那麼組織民族誌提供你跳出框架的方法,做出關於你真實經驗的知識,以這個作為知識的根據。所以受惠於組織民族誌的人一定不只有處於弱勢的女性。
問四:Dorothy提到他從馬克斯學到兩個東西,第一個是要從實際的人,所做的活動出發。之後Dorothy又詮釋了兩個概念:統治關係和綜合體組織。這樣的方法,作觀察的時候有沒有特別要看的東西?有沒有既定的立場,或存在心中的預設?另外,能不能舉例子說明要怎麼在研究中看到統治關係和綜合體組織?
答:你要看什麼,可以看到統治關係,取決於你的研究問題。你的研究問題會決定你要看什麼。一個重點是,講工作流程時,所謂工作不是勞動市場的有籌工作。只要佔用你的時間心力,都是工作。比如說一群女性主義研究者在看家庭的無償工作時,就記錄了很多這樣的工作。所以看工作時,定義很廣。另一個例子是一個老人看護的工作,研究者自己是看護,做參與式觀察。她發現住在護理之家的老人也有工作,一群老女人等待早餐也是重要的工作。而接受服務時也要表達感謝這樣工作人員會對你比較好。這也是工作,這樣對工作的看法,在組織民族誌裡比較有用。像在大學裡,工作不只是上課。學生們從一個教室趕到下一個教室去,也是工作;要是所有學生沒到那間教室,大學的課程就無法進行。這些都是看不見的工作。我自己先前提到的研究就在問,為什麼學校很重視雙親家庭,所謂正常的家庭。我們先訪問了低收入戶家長,之後又訪問老師每次的研究都讓我們多發現一點。這個過程很像在解拼圖,從自己的實際生活出發,一步一步慢慢地發現。每次問的問題不是一樣的,不是先設計好一套問題去取樣本,都問同樣的問題,再來作分析。這就很像地圖,有次我去滑雪,飯店已就有一張滑雪的地圖,告訴你每一條路怎麼連結,哪作山在什麼地方。我們從自己的經驗出發,看尋統治關係也會發現所有東西都連結在一起。這種連結很無止盡,可以連到整個世界去,所以作研究時有時候必須採煞車。
問五:作組織民族誌似乎是在告訴別人真實是什麼,因為相嵌的關係是自己不會看到的。但對我來說,研究者一定是透過理論的眼鏡,他相信某理論或偏什麼理論。但你做出的研究可能與其他人所相信的理論相左,那這樣要怎麼說服別人相信自己作的研究是真實的?
答:我不打算進入認識論理討論何謂真實的辯論。作組織民族誌並不是把自己所認為的真實強加在別人身上,而是盡可能地嚴謹地說明這些事情經過什麼程序組成起來的。你可以宣稱自己發現的東西,但不能說是絕對的真理。而當別人給你意見時,你會發現更多,就可以修正你的東西。這是個開放的宣稱。
王教授答:Dorothy作的研就跟我們一般的質性研究不一樣,要去強調主觀經驗是絕對的對。他認為這些主觀經驗也是社會建構起來的,所以你要分析這些主觀經驗背後組成的被客體化的流程。主觀經驗和真實世界之間經過反思生產出來的詮釋才是重要的。所以他會強調自己是反思,但不宣稱自己生產客觀知識的社會學。
問六:我是因為這一連串的演講才知道什麼是組織民族誌的研就法,有點遺憾自己現在才認識。我現在在做的是產前母血篩檢的研究,然後我就從媽媽的經驗,他們講自己的故事開始研究。但瞭解到一個程度之後,握實在覺得我如果早一點知道這個方法,也許過程會輕鬆一點,更清楚一點。不會到現在,脈絡才慢慢出來。我想問的是,Dorothy怎麼認定自己是女性主義的學者?他對女性主義的學者有什麼樣的期許?
答:我認為自己是女性主義者,但沒有特別說自己是女性主義學者。不過我實踐女性主義的方法比較主要在學術工作上。我不太想去定義怎樣才是夠格的女性主義,女性主義的定義很簡單,就是站在女性這一邊。這個講法在不同時候不同脈絡下會有不同的意義,不過這樣就夠了。
問七:請界定一下組織民族誌是個方法,觀點,還是方法論。再來是,如何在研究裡找到統治關係,關連,還有看不見的東西怎麼找出來?你跟一般的民族誌有什麼不同?他們也都看關連,看隱形,要是研究作的好自然就會深入到這個。請你幫自己辯護一下,你說是與眾不同,沒有淵源的組織民族誌,跟其他的民族誌有什麼不一樣?
答:有些人對把組之民族誌說是方法論,但我會說他是一種另類的社會學,會跟隨著探索研究。我不想把他變成一種既定的概念化的有具體步驟可以操作的方法論。一般民族誌學可以觀察的東西都被界定為在地可以觀察的東西,但組織民族誌應該要超越在地,看到文本如何透過工作流程把事情組合在一起,發展一種進入巨視面的分析。這中間,文本是很重要的。至於要怎麼作研究,歡迎你們聘用我或我的學生來為大家上一學年的課,三言兩語應該無法說明白。
問八:我家小孩也很頑皮,所以我很同意媽媽被責怪的情況。我想要問文本是指什麼,僅限於書寫的文字嗎?因為我作日誌時期的科學育兒研究,因為歐美在二十一世紀初開始有一批專家,像你講的心理學專家或是兒童發展專家,寫很多書教媽媽要怎麼養小孩。台灣也開始有這些書,叫媽媽要照著書養小孩,但是因為媽媽不識字,叫他們去那邊諮詢也不去,所以專家在那個時期很挫折。那母親可能依賴自己的身體經驗,像是哺乳來作母職的實踐。所以我想從這裡問,文本是不是適用用於特定的社會或特定的歷史時期?
答:這個問題要回到真實的情況回答。三零四零年代在美國中西部有很大的母職轉變,之前的母職實踐大多事從母親那邊傳下來的,但從那時候開始有越來越多政府的參與,宣導母職。你提到台灣的母親不用文本,而是靠自己的經驗。不用文本就不用文本,那就要去探討這些不用文本的母親如何實踐他們的母職。所以這是要依照你實際的情況來作看。
主持人:我們謝謝Dorothy。
Dorothy:很謝謝大家邀請我來,並且提出這麼有挑戰性的問題,這使生活更有趣。
附錄:高醫大(11/16/2004)上午11:30∼13:30師生座談
Dorothy Smith
在高醫大學性別所的午餐聚會師生座談會。性別所的師生們向Dorothy提出不少學術與生活的問題,她均耐心地一一回應,告訴大家她單親的經驗、女性學者在學術圈裡的位置、以及她對於社會學理論的思辯。整個活動持續一個半小時,圓滿結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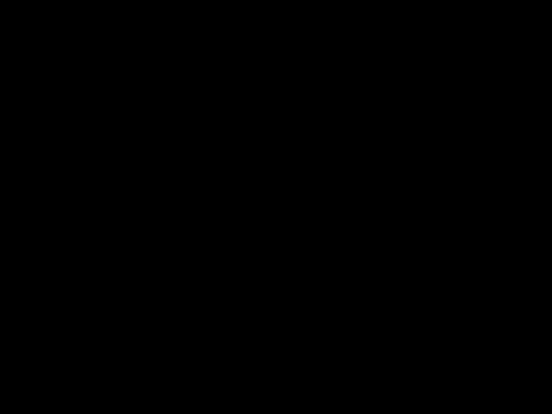
照片說明:Dr.
Smith 左旁一為座談主持人高醫性別所林津如教授,左旁二為陳美華教授,右旁一為王秀雲教授,右旁二為成令方所長,其餘為性別所研究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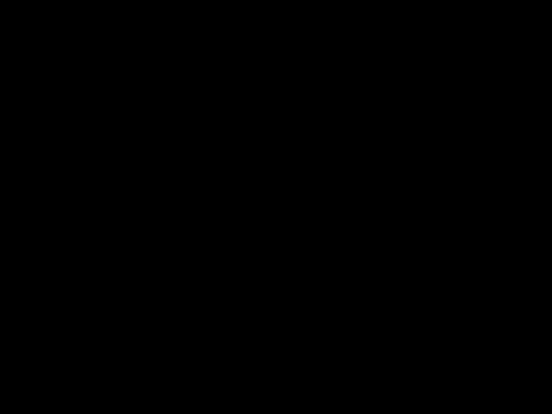
照片說明:Dr.
Smith與高醫大性別所師生座談時專注的神態